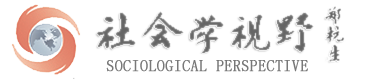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人民的选择?
——收视率背后的阶级与代表性政治
张韵 吴畅畅 赵月枝
原文载于👩🍳🐘:《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内容提要】收视率是人民的选择吗?在市场话语的主导下,收视率被视为传播效果的“客观”反映和一种“民主”的表达。出于对这一说法的回应,本文试图揭示🏘👩👩👧,收视率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构性产物,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在中国,收视率的商品化和收视率调查的制度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与电视媒体的社会主义属性之间形成张力🚡🛰。本文认为,“收视率是人民的选择”作为一种市场话语,简化和遮蔽了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化矛盾及媒体的阶级与代表性政治🩳🧔♀️。在由政治与经济权力共同主导的中国广电系统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收视率的商品化和制度化使“受众”取代了“人民”🪇,使资本积累的目标取代了建设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违背了体现“人民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媒体的建设和发展宗旨👨🏽🚀。
【关键词】收视率 中国电视 人民 阶级 代表性政治
一、引言
“收视率是人民的选择”。这是2014年3月5日,中国电影导演冯小刚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文艺界别委员小组讨论上被媒体捕捉到的发言。在演员宋丹丹针对现今电视节目恶性竞争🧠🏊🏽、价值观混乱的现象呼吁“只有有正确价值观的收视率才是有价值的收视率”之后,冯小刚发表了此番言论⇒:“只要是收视率的调查,没有所谓正确不正确,所谓的收视率就是大多数的抽样🏄🏿♂️。只要是真的收视率,都是观众的选择⬛️,尊龙凯时娱乐都应该尊重,但造假肯定是不对的🦉,尊龙凯时娱乐要相信,真实的收视率是人民的选择🚣♀️,人民是最有智慧的🧔🏿♂️。”①这位以表现“市民文化”的商业片见长的著名导演的说法🤟,无疑代表了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一种对于收视率的认知🏝。
2015年两会上👨🏻🚒,两位电视业界人士相继发表关于收视率的看法,再次引发收视率造假的讨论💄。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前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总经理欧阳常林表示,现在很多电视台存在收视率作假现象,背后有专业公司操盘,“这个问题到了该抓的时候🫶🏿,尊龙凯时娱乐在主流媒体阵地要弘扬正气”🪪;同日,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在河南团开放日上批评收视率🦹♀️,指出“甚至有人花钱购买收视率”,这是“文化的巨大隐患”。②两位电视从业者的批评👝,同样代表了电视行业内部对当前收视率调查数据的一种态度。这一态度仍然以对电视市场化及其奉行的收视率逻辑为基点,呼吁一种“公平”、“真实”的电视行业竞争规则。
收视率之所以在电视的节目制作编排🧄、节目评价及广告投放决策中占有关键作用😅♔,因为行业认可其作为“科学”的观众测量数据👳🏼,能够“客观”地反映观众的收视行为和意愿🚥,体现大众文化。更有甚者认为🦅,“收视率是一种投票,一种决定受众想看的系统”👩🏼🚒。③通过这样的观点,收视率被认为是一种“数人头”,有点类似民主的“多数决”🧁,收视率等于是以行动来表达民主的一种方式💫🧑🔧,所有的观众与听众都可以在娱乐、新闻、资讯等广大范围中自由选择。④另一方面,针对电视荧屏上暴力、色情泛滥等乱象☯️,诸如“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之类的批评质疑也不绝于耳🏄🏽♀️🙎🏿。通过这些言论,媒体精英们表达了对“广播电视行业盲目追求收视率所导致的电视节目品质低劣化”现象的深恶痛绝。在学界,也有研究者指出了“收视率导向”背后的商品化本质。⑤然而,不管是媒体人的道德主义偏见还是学界的批评,都没能对收视率是“科学”、“民主”的说法做出有力回应🙇🏻。针对收视率的另一种普遍看法貌似理性客观🖖🏿:收视率不是万能的,只是反映电视传播效果的指标。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作为一种行为指标和量化工具🔫,收视率的市场价值是需要肯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收视率调查方法,合理运用收视率🏋🏽♂️🛍️。⑥
收视率是否为一种客观的反映?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主导下的认识论,为将收视率自然化和合理化提供了空间。在对此类观点进行剖析之前🧑🏽🍼,首先涉及对作为一种媒介技术的广播电视的理解🤔。传统传播理论将电视看作一种技术工具,热衷于对其传播效果的研究。然而,不加思索地将“电视技术造成了各种社会变化”的说法当作应然的前提,脱离语境、过程且遮蔽了社会动因的“效果”研究始终是流于肤浅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直接推动电视技术发明和发展的社会需要、社会目的和社会实践是在各种社会“意向”(intention)中形成的🦖,而广播电视制度是据人们预先划定的特定社会模式与科技条件发展出来的。⑦亦如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观点:如果将技术看作自主中立的🧒🏼📡,就会忽略电视技术诞生的社会背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文化,在广播电视技术和制度系统的建设发展过程之中,就会不加甄别地受到技术背后的“意向”🧑🏽🦰,也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影响。⑧内在于中国广播电视媒介系统市场化进程之中的收视率的商品化过程正是如此🙅🏿♀️🫑,而这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及广播电视体制的社会主义属性产生了矛盾。
“广播电视是技术的一环,有赖于社会制度的配合,更是文化生活的寄托。”⑨收视率调查作为一种商业行为,介入了与中国广播电视技术系统相关联的制度系统的形成过程中👩🏼🦲,并与电视文化发生了联系🌌。因此,如果简单地将收视率视作电视传播效果的客观反映👩🏿💻,而不厘清中国特定政治经济语境下收视率商品化对媒体与人民关系的影响🌍,尊龙凯时娱乐就只能一边目睹以收视率为基础构建的价值观混乱、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猖行的电视文化景象,一边面对收视率“民主”说深感矛盾而无力反驳。收视率这一“看似客观的关于观众的数据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创造——政治经济因素的结果”🧑🏼✈️。⑩为此,尊龙凯时娱乐需要思考的是:收视率是如何产生的?收视率的所谓“科学性”来源于哪里?在中国语境下👫,收视率如何参与了广播电视媒体的变革历程𓀉?收视率在国家🐒、媒体与人民的关系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一切又是如何裹挟于中国媒体与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变革之中的👨🏼⚕️🎈?
二™️、拆解收视率🧑🔬🏺:科学数据还是媒介商品?
收视率最初是由无线电广播的收听率发展而来的。收听率调查之所以在美国出现并受到重视,是因为广告商开始意识到电台广播的市场潜力,需要有形的调查数字来确知看不见的听众🌬。1120世纪20年代,美国无线电商业广播电台因刺激收音机销量的需要而出现,广播电台补贴节目制作费用的途径之一🌿,便是以在广播节目中推销产品为条件获取厂商赞助⛹🏿♂️。到20年代中期,广播网出现并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告工具。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媒体获得特定的消费者,广告商和广播网开始寻求一种对听众进行测量的方法。然而🗯,在听众数量的评估结果上,广告商和广播网之间是存在利益分歧的♍️。121927年😁,美国的全国广告商协会(ANA)和广告代理商协会(AAAA)开始拒绝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自己发布的听众评估报告,他们质疑广播网为了提高广告价格,获取更高的利益,会夸大其所拥有的由主动消费者构成的受众的数量和质量。为了使广告商能以更低的价格从广播网那里购买到广告时间,全国广告商协会和广告代理商协会雇用了市场调查者阿奇博尔德·克罗斯利(Archibald Crossley),请他设计一个受众测量的方法,希望测量所得的收听率能够使他们在广告价格谈判中获得优势。克罗斯利从电话号码簿中获取随机样本,请受访者回忆前一天晚上收听的广播节目👩🏿🦰,后又采取每15分钟进行电话抽样访问的方法🕎,调查受访者的同步收听行为💛。最早的、以电话访问为基础的收听率调查方法由此诞生。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随着电视传播以广播网为基础逐渐兴起💆🏻,收视率调查也开始发展起来🔯。在一个将大众仅仅视为市场竞相角逐的对象的广播电视系统中,收视率出现之初就是服务于商业意向🦯,而不是为了获得观众意见🧛🏻♀️👊🏽。收视率调查的最终目标是作为特定消费者的受众,而不是一般的公众。这也就是斯迈思所指出的受众商品化(Audience Commodification)的过程🕵🏽:“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大量生产、由广告出资支应的传播,其商品形式就是受众与读者群(audiences and readerships)⛹🏿。”13广告费支持的广播电视媒体提供作为“免费午餐”的节目内容,目的是引诱受众来到生产现场——收音机或电视机前👦🏿,媒体再将生产出来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于是,受众就成为了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而收视率调查公司的工作就是收集特定受众的社会经济资料,由此他们可以迅速而专业地评估广告商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受众商品🙇♂️。14测量受众的公司能够计算受众的数量多寡🤞,并区分各色人等的类别,然后将这些数据出售给媒体和广告主💅。媒体则根据“产品”(受众)的数量和质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人口指标)的高低🤘🏻,也就是购买力的强弱🏅,向广告客户收取费用🈚️🌟。“高质量”的受众即目标消费者与一般公众之间的差异*️⃣,一开始就是作为收视率出现的条件而存在的📥。在此基础上,米汉(Eileen Meehan)进一步指出收视率就是商品👍🏻,关于受众的数量☝🏻、组成及媒体使用模型等资料的报告才是媒体系统的主要商品。15
收视率数据之所以能够顺利应用✮,是因为本身是商业性质的收视率调查,却一直以科学的面貌出现🔇。16当下的收视率调查依托于特定的技术手段🧘🏼♀️,但其所谓“科学性”,是在不断协调收视率市场中广告商、广告代理商和广播网的利益👩🏻💻,新的调查公司不断占据收视率垄断市场的过程中建构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的限制决定了收视率调查公司进行的并不是关于观众的社会科学研究”🤢。17最初,收听率产生时🧑🌾,美国的电话服务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市区和城镇,且住宅电话并不普及,家庭拥有一部电话和一本电话簿在当时实际上是地位的象征🤦🏿♂️。克罗斯利的样本对象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也能够用得起电话的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通过这种电话调查的访问和样本,是不能得出有关一般人口收听情况的合理准确数据的👺🐌,但这些具有经济实力的调查对象恰恰满足了广告商对真正的消费者的需求,他们需要的本来就不仅仅是收听电台广播的人。因此,依照这种逻辑发展起来的收视率也不是单纯的研究成果🏵,它们是企业为取得经济成功而设计的工具,统计模型的选择基于经济目的👩🏽🔧,而非社会科学原则。18
在实证主义效果研究范式的主导下,焦点被聚集到了对调查统计方法精确性和��科学性”的不断追求上🙌🏿,似乎所有关于收视率代表性的问题只是由于调查技术还不够完善,却掩盖了媒体及调查公司所渗入其中的商品化逻辑🐪。收视率调查公司建立一系列包括基础研究、抽样和建立固定样组🍎、测量🚕、统计和数据处理的复杂过程,其目的在于平衡收视率市场中的各方利益👯♀️。因为收视率数据为电视台、广告主和广告代理商服务🤳🏽,但调查方法的差异会使调查数字膨胀或缩小,广告价格就会有所争议🧠,“科学”的调查方法和具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数据则可以取得“客观”的立场来调和这种矛盾。正因为如此,收视率的调查技术可以成为相关公司进行市场控制、获利或是降低成本的竞争策略7️⃣📍,并由此形成一个制度化的收视率垄断市场🟩。19如果要形成对垄断者的挑战,一家新的公司需要在平衡和满足各方面共同需求的基础上,开发新的技术,使自己与原垄断者的产品区别开来。然而🌂,新的收视率测量的仍然是受众规模和人口特征,差异只在于获取信息的方式🔈。所以👃🏻,发明了测量仪收视率的AC尼尔森公司得以超越电话调查法📼,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垄断美国的收视率调查市场🙎🏻♂️🛍。
三✷、从观众来信到“通用货币”🐜👋🏼:中国收视率的商品化进程
在中国🐹,收视率的从无到有,再到收视率市场的形成和扩张,其过程深嵌于广播电视系统的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之中;同时,收视率作为电视媒介融入一般性经济过程的关键因素🈷️,对广播电视及其产业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
尽管早在1979年上海电视台就成立了广告业务科,并播出了中国内地第一条电视商业广告🏠,但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由中央电视台首先开始进行全国观众抽样调查和收视率调查统计。在此之前🧑🏼🎓,传统的观众意见采集模式以观众来信来电🐓、召开座谈会及访谈等方式为主。例如🫶🏿,中央电视台一档名为《为您服务》的栏目在1983年收到四万多封观众来信🌽;198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专题片《话说运河》甚至采用边拍、边编🏋🏽♂️、边播的方式,根据观众意见反馈随时调整节目方案,吸引了大量的观众🚼。20彼时,国家财政对广电系统进行全额拨款的政策已经做出调整,“四级办电视”方针所推动的电视系统的商业化进程开始启动,但广告和市场尚未成为中国电视业发展的要务。虽然电视台和频道数量增长,但行政色彩鲜明,其覆盖传播的范围也局限在本级行政区域内✍️。同时,电视作为重要的文化场域,在享受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的同时,亦未受到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的过分浸染。21在内容上,以新闻🧑🎓、电视专题片、电视剧等为主要内容,体现传达信息♏️、宣传思想、引导舆论和提供服务的职能🕰🦵🏽,一方面是“推动国家现代化计划的主要工具”,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推进其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思想的积极论坛”。2280年代中后期🏀,“收视率”一词随着有关西方电视传播的评介文字被引进,与开始登陆中国的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理论所带来的“媒介”、“受众”、“传播效果”等概念一起🧛🏿,逐渐改变人们对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的认知🧿。与传播学理论相伴而来的运用社会科学手段研究受众及传播效果的方法,以其“科学”、“客观”的形象对电视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相较之下🤦🏼,传统的观众来信这类质化的意见采集方法就显得特别“主观随意”。23
1986年🚵🏽♂️🤜🏿,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委托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进行了“全国28城市观众抽样调查”,随后与北京市统计局合作进行了“北京地区农村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同年6月开始进行以晚间黄金时段为主的日常电视节目的收视率统计🌱🛌🏻,上海、广东等电视台也相继采用抽样统计方法进行观众调查,收视率调查正式在中国电视行业开始被使用。1987年下半年💬,由中央电视台牵头💂🏽♂️,联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大规模的“首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电视观众人数已达6亿,大部分观众最重视新闻节目🏍,文化程度较低的观众喜欢“有情节🫥、故事性强🛢、能娱乐消遣”的电视节目👩🦳,文化程度高的观众欣赏“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电视节目”✝️。同年✳️,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又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对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的调查研究,采取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综合考察。241991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建立“全国电视观众调查网”,经过三年的建设铺开🧑🏼⚖️,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五十多个调查站🎼,从观众的基本情况、媒介行为🎯、心理感受三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
与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实时的收视率调查不同🤏,中国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出现之初带有非常明显的非市场化特征。251987年启动的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每5年进行一次👸🏽,旨在了解全国观众对中央电视台和各省级电视台节目的收视情况,主要用于节目效果分析与内部参考,和广告市场没有太多的关联,抽样调查的执行机构也不是独立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网”由中央电视台主持并提供设备和运行费用,地方台负责对设在本地的调查站进行管理👂🏻,中央电视台每年要投入大量财力和人力进行抽样统计调查方法培训,维持调查网的正常运行🦹♀️。花费巨大所得的调查资料主要用于中央电视台和各个省台进行节目效果分析。获取观众对电视节目的意见并作为电视自我反馈依据是早期收视率调查的主要目的和作用。
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正式确立👩🏻✈️,市场力量开始席卷中国的传媒系统。同年6月,传统上由政府财政支持的文化宣传机构被列入“第三产业”,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发展被上升到媒体产业政策的高度,中国电视系统开始了与国际电视接轨的市场化进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逐渐培育了一个需求不断增大的广告市场,电视节目市场得到发展。相应地,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电视台和频道数量的迅速增长。1996年中央电视台由1个频道扩张到8个频道,各有线电视台纷纷创办专业频道,各省级电视台陆续上星。技术、设备投入与规模扩张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在自负盈亏加入激烈市场竞争的过程中,电视媒介为了提高广告收入🧑🏼🦰,吸引更多的观众,开始重视西方的收视率调查方法🦹🏿。此时,电视业界普遍达成共识,即之前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过程中🧑🦼,“电视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与国外通行的对调查机构客观、科学➜、中立的要求显然有距离”。26由此可见→,原本中央电视台自主进行的、以获取观众意见为目的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无法满足电视媒介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市场对“客观”🤶🏽、“实时”的观众数据的需求。
1996年,美国AC尼尔森媒介研究公司(ACN)通过收购调查研究集团登陆中国,它采取的策略是首先进驻大都市,并在上海设立了调查点👘。次年,央视调查咨询中心(CVSC)与法国索福瑞集团(Sofres)合资👍🏻,正式注册成立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CSM),“旨在为传媒市场提供全国性🥽、连续性、独立的、有代表性和产业化的服务”🤍。央视-索福瑞的中方合作方“央视调查咨询中心”成立于1995年👮,其前身是央视总编室观众联系组🎲,“全国观众调查网”的建设正是由这个作为党和人民宣传机构的国家事业部门所主导🤵🏻♂️。与央视脱钩后,央视调查咨询中心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它以原来的观众调查网为基础📗,将收视率调查纳入市场化经营管理体制中,标志着中国收视率调查走向市场规范的开端👨🏿🏭。短短几年时间内🦹🏼,收视率与广告挂钩👜,不仅推动了电视媒介的市场化,而且迅速形成了一个收视率调查市场👨🏿🔧,完成了从观众反馈机制到广告交易“通用货币”27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奉行的群众路线下的国家、媒体与人民的关系,逐步被纳入到全球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市场机制下的广告、媒体与受众的三角关系之中。
一方面,央视-索福瑞公司成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国际4A广告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因为急需可供参考的数据来评价电视媒体的广告投放价值,当时13家在中国内地开展业务的国际广告公司和5家电视台发出一封共同签名的倡议书,对媒体调查机构提出“独立🧏🏽♂️、全国性、连续性、技术先进和公正透明”五点要求🎖,索福瑞借机将产品和业务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央视调查咨询中心自独立之后,迫切希望通过与索福瑞的合作🫂👩🏻🦯➡️,弱化其央视背景,以树立公正、独立的第三者形象🧑🧑🧒🧒。长期以来,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进程不但被理解为中国媒体制度与西方媒体制度“接轨”的途径,而且被认为是符合了某种普世和客观的“发展规律”✈️。28在引进之初依然延续了群众路线传统的全国电视受众调查,正是在这种认识论的“引领”下🧎🏻♂️➡️,一步步转变成以商业化、市场化逻辑为基础的收视率调查。
央视-索福瑞在建立国内收视率调查网络时🤞🤓,相继建成全国网🌏、省会城市网,以及涵盖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城市网⬆️。这些不同组合的调查数据👨🏼🦰,与国内省级卫视的发展密不可分。一开始,省级卫视在各地的落地并不均衡。在省级卫视向索福瑞购买数据形成的商业关系中,每家省级卫视都可以获得“定制”的收视数据🧑🏼🍼。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向广告商汇报收视表现时显得更加“好看”。譬如👷♀️,湖南卫视由于没有在大连落地,在对外公布使用全国网数据前♞,一直采取CSM29城市快速检测数据。同样,东方卫视早前使用全国网🧜🏿♀️🏄🏻♀️,后来采用CSM34城市网数据,而包括江苏卫视在内的绝大部分省级卫视则坚持使用CSM44城市快速检测数据。由于不同的组合形成的数据当然不一🧖🏽♂️,因此,21世纪初期👷🏿♀️,许多省级卫视都对外宣称💂♀️,自己的节目在黄金时段收视率或收视份额全国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由于全国网的收视抽样更加随机,而城市网的样本户相对固定,自2009年起,关于数据造假🧑🏻🦯➡️、公关公司购买收视数据等新闻就不断见诸媒体。例如,一线省级卫视的电视剧经常出现要么在某地的收视率为零要么居高不下等收视异常情况。2008年🙎🏻♀️✡️,国内的一次调查研究显示,电视从业者认为“缺乏中立的监督稽核机构”29是导致收视率争议的重要因素之一。收视率作假的直接动力,还是来自于省级卫视市场化与商业化过程中对节目利润的非理性追求,否则尊龙凯时娱乐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尽管崔永元等知名媒体人、业界和知识界人士高调声讨收视率,并倡导收视调查体系变革,可索福瑞的收视数据依然成为媒介与业界衡量节目优劣的首要标准🏏。实际上,这绝不是收视率调查机构垄断所导致🧑🏽🍳,而是广告与市场化逻辑已经在电视产业发展过程中根深蒂固的直接结果。
目前,一家垄断是各国收视率调查的普遍常态,由于收视率调查的技术和成本壁垒,全球大多数市场的收视率调查都掌握在少数国际公司手中。302008年🤥🍩,尼尔森公司退出中国收视率调查市场,尽管与央视-索福瑞对垒多年始终处于劣势,尼尔森的退出却不仅仅是竞争失败那么简单。早在2004年8月,尼尔森公司和当时世界第二大传播集团WPP下属的凯度集团(Kantar)合资创立了AGB尼尔森。2008年9月,WPP集团以11亿英镑收购全球第三大市场研究公司索福瑞集团(TNS),而索福瑞集团正是央视-索福瑞的股东之一。由于欧盟的反垄断条款,加上央视-索福瑞和AGB尼尔森的直接竞争,WPP集团必须在卖掉索福瑞集团在欧洲的视听率调查部门与出售其所持AGB尼尔森的股份之间做出选择。同年11月11日,WPP集团以股权置换的方式退出AGB尼尔森𓀌,为控股央视-索福瑞扫清障碍👨🏻🎤。尼尔森公司则成为AGB尼尔森的唯一股东,但由于对WPP集团旗下奥美、群邑等广告代理公司和媒体公司的长期依赖难以为继,而选择退出中国收视率市场。31于是,在中国电视收视率调查领域,出现了外国资本一家独大的垄断状况🔲。
然而,在争议中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往往是索福瑞的央视背景,少有人将矛头指向真正掌握着市场命脉的WPP集团🤴🏼。作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传播集团,WPP集团旗下的广告公司和媒介集团掌握着宝洁🧓🏽🔣、强生💇🏽♂️☃️、戴尔、壳牌、福特等一大批大型广告客户的投放和策略🧔🏼♂️🧙🏿♂️。也就是说🪮,在广告价格与收视率挂钩的情况下🗣,代理中国内地电视台每年数百亿广告投放的商业集团🧃,同时也是中国收视率调查垄断机构的股东。2009年,以视听率调查和媒介咨询为主要业务的泓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次年🧘♂️🦆,尼尔森公司宣布与北京中传网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重回中国收视率市场🐂。中国收视率市场似乎重新开启了竞争模式,两家公司都宣布将展开针对数字电视的收视调查新业务⬇️,但在一个制度化的垄断市场中♿,利用新技术展开差异化竞争是必需的无奈之举,最终不会改变市场的垄断结构🧑🚀。
四🧑🏻🦲、受众即人民?收视数据的代表性政治
收视率在中国经历了从由“观众联系组”主导的意见反馈机制,到转型为市场化之后迅速卷入跨国资本集团不断兼并、垄断大潮之中的商品化的过程🫴🏽™️。当前🪅,电视业界流行一句话⏳,“收视率高的不一定是好节目,收视率低的一定不是好节目”🚟,表达了以收视率商品化为基础的电视市场化改革制造受众🏊🏼♀️、取代人民的逻辑之后⛔,衡量电视节目的一种悖论。然而,收视率依然反复被拿来标榜其作为“人民的选择”所体现的“民主性”。各种话语博弈、意识形态冲突和文化张力背后,体现或被遮蔽的是怎样一种媒体与国家、人民的关系♙🌎,而收视率又是如何参与到其中的?
在市场逻辑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收视率对社会文化的作用体现在,通过媒介购买时段的方式与节目评估体系🧑🏿🔧⚒,影响电视节目的内容生产和编排。从2002年起,央视开始实施《中央电视台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条例》,《电视你我他》🧑🏿🎓🚶🏻♀️、《综艺大观》等栏目因收视率过低而被停播的消息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尽管央视公开解释收视率并不是唯一标准🌘,对栏目进行警示和淘汰,所依据的是以客观🫶🏽、主观和成本指标组成的综合节目评价体系🙎🏿♀️,但是,在收视率与媒介购买机制挂钩的前提下🏋🏻,高收视率对电视台来说就意味着高额的广告收入🩰。对历年广告招标金额不断飙升的央视而言🍉,收视率尽管不是唯一💇🏽,却也是极为重要的指标。2011年7月,央视终结了“末位淘汰制”⛲️,新的评价体系以引导力(20%)🧏♀️、影响力(25%)📛🙍🏼♂️、传播力(50%)、专业力(5%)四个一级指标构成,以收视率调查数据为基础的传播力依然占据了最大的权重。相较而言⚄💟,这一比例在全国来说却是不高的。绝大多数电视台的评估体系中⏩,收视率指标所占的权重都超过了50%,有相当一部分超过了70%。在以成功的市场化和娱乐化运作为标志的湖南卫视,节目评估指标则完全由收视率、市场份额以及以收视率数据为基础的收视负载比、负载点盈利和点成本构成🏷。32
将收视率置于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的核心位置👩🏽🦰,这种行为的弊端极为明显,以至于在广泛的批评声中,收视率在节目评估过程中的比重问题被当作了替罪羊,从而掩盖了真正的症结所在。典型的观点是:“收视率主要反映观众数量👩👧👧,要反映节目在观众心目中的质量✍️,还需要引入满意度指标。收视率指标之于社会效益而言🅱️,应该是基础之一、要件之一。”33现实的情况是🗝,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分所造成的无可弥补的张力中👩✈️,无论是提出引入“满意度指标”、“欣赏指数”还是“收视率全效指标评估体系”34,都没有带来根本的变化。强调以补充性手段弥补收视率带来的“社会效益”缺失👧🏼,实际上是不断强化收视率在“经济效益”层面的合理性,从而掩盖商品逻辑本身对“社会效益”的遮蔽与损害。在广播电视系统产业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这是市场力量及其话语占据优势地位的体现👨🦱。
即使面对着行政力量的不断挤压与规制,这种市场力量依然通过收视率非常直观地作用在电视节目内容生产上🥨🏆。以综艺节目为例,题材撞车🈲、节目同质化现象屡禁不止。继选秀节目泛滥被叫停之后,从名称到内容形式都雷同于2012年浙江卫视热播节目《中国好声音》的《中国最强音》、《中国好歌曲》、《中国梦之声》等歌唱类节目密集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2013年末“加强版限娱令”对歌唱类选拔节目的数量和播出时间做出限制,35亲子节目又借势在《爸爸去哪儿》取得高收视率之后扎堆出现🏩,《爸爸回来了》、《爸爸请回答》、《老爸老妈看我的》、《宝贝看你的》等令观众应接不暇🧑🏼🔬,其中既有**的“本土原创”节目,也有国外版权引进节目。不论是原创还是引进👨🏼🍳,不同的生产过程却导致了相似的节目模式和内容,同质化的节目大量占据频道资源,这是谁的选择?在国内广告市场交易过程中,广告商为规避风险倾向于选择已取得高收视率的节目。在广告投放成为综艺节目最主要收入,一档节目通常靠冠名和特约就能摊平成本的情况下🚨,缺少广告商的投资💅🏿,节目制作费用就会打折扣,一系列商业流程也不能正常运转。因此🚵🏿♂️,电视台跟风引进或模仿同类综艺节目反而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36
“在现存广电体制中👡,电视内容的组织及随之而来的观看体验👷♂️,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一种事先安排的连续的流程。”37“流程”的概念是威廉斯根据自己初次接触大量插播广告的美国电视的经验而提出的。根据威廉斯的观察🧣🥴,首先,电视的内容是连续有机体,不是各节目的分散性聚合,而是整体的“流程”。所有为商业体系所制作的电视节目,从构思到播出,都是流程的一部分。传统机制下中国电视媒体节目内容选择与节目编排关系并不紧密的情况已经改变。广告商之所以宁可投资有抄袭之嫌的节目也不愿大力支持一档全新的节目,是因为无论购买版权还是对版权的抄袭,都是对既有知识产权的消耗🧝🏿♀️,而不是投资再造,成本相对更小👮🏽♂️,而这种消耗的前提在于🪀,它天然存在准确的忠诚度,符合市场逻辑下风险核算的标准。如今🧶🪟,从“黄金时间”到全天候编排,再到季播和无缝编排策略,电视节目编排播放的不断调整👙,被业界称为是从缺乏营销意识转为以市场和受众需求为导向,再到以培养观众忠诚为目标的不断进步,实现了由电视台主导向“观众主导”的转变👨🌾。38
然而,电视节目的编播,包括节目内容选择、编排♑️🚡、推广和评估,作为一个整体会对观众注意力产生影响。这也就是威廉斯所揭示的第二个层面,即“流程”使传播者在电视内容和观众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具有把观众卷入其中的能力,进一步而言这体现了传播者和观众之间的控制关系——利益阶层利用电视,运用“流程”这一电视形式👍🙎,吸引和控制大众,或为频道竞争获取商业利润,或为达到意识形态宣传目的⭐️🏌🏼♂️。在市场化运作条件下,与其说让观众满意是节目编排的要务,不如说“如何防止观众有意识🙇🏼♀️、有规律地在广告时段换台已经成为保障节目收视的关键环节🔘🕵🏽♂️,如何安置导致观众大量流失的硬版广告是编排工作的重中之重”。39所谓“观众主导”并非观众意见影响节目编排,而是电视台利用节目编排扩展广告效果空间🕵🏿♂️,影响收视率所反映的观众数量👩🏼🦰。
各级电视台在内容生产编排过程中对于收视率标准的倚重,既反映也加剧了电视媒体间的竞争。湖南卫视等地方电视台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开始挑战央视的垄断地位💁🏿♂️。但在无法与央视所占据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象征资源相抗衡的情况下,各省级卫视台最终选择了“非政治化”的发展策略。40以娱乐化成就商业化的湖南卫视,在收视率持续攀升、经济实力大举提升的过程中,一起风生水起的还有其在大众文化领域的话语权。41继2005年“超女”引发巨大社会反响之后,2009年8月湖南卫视单月CMS22收视率首次超过央视,这些都被宣称为“人民的选择”,被解读出了民主的意味。作为电视业界的“通用货币”,收视率能否以及如何体现出“人民的选择”💔😉?受众使用遥控器对节目的选择🤵🏿♀️,难道真是一种收视民主的表达?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分析西方电视运营机制时曾经指出,通过收视率的作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电视一方面具有非政治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可以把非政治事件政治化👲。这种双重功能使得电视成为威胁社会民主的一种危险的符号暴力👨🏽⚖️。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电视到底代表谁的声音?42尊龙凯时娱乐需要接着继续追问🆙𓀑,在中国电视市场上👩🏽🎓😇,收视率数据到底代表了谁的收视行为🙎♂️?反映出谁的喜好和趣味🔬?不可否认🙆♀️,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基于受众消费能力的“一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的商业逻辑所导致的是大众文化产品的中产阶层趣味偏向🍳🏄🏿,以及对下层劳动者话语权的相对排斥。43首先,如前所述🪀,央视-索福瑞提供CSM146城市网(包括CSM35中心城市组、CSM71城市组等数据组),CSM25省网和CSM全国网等不同的收视率数据,而大多数电视台与广告商更偏向和看重城市网数据🚓,CSM全国网数据只有包括央视在内的少数使用者🤵🏿。全国网和城市网样本户因技术条件的关系,都采取日记卡与测量仪并行的调查方式🏋🏿♂️,虽然全国网覆盖城镇和��村地区13亿人口,样本量由过去的5000户增加至当前的8000户🫰🏽,收视绝对误差在1%之下,但是,覆盖国内省会城市或大中小城市的各大城市网数据还是广告商青睐的对象。这是因为🤷🏻,大城市网数据能从大体上反映出城市消费者群体的收视习惯,后者正是广告商看重的最具消费活力与购买力的人群。
其次🧚🏿♂️,直到最近几年,收视率的调查数据才成为热点。与此同时🫴,收视率的数据呈现越来越精确👄〽️。2012年以前,城市网的收视率只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2013年以来🫲🏿,数据开始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表面上看,小数点后几位的差别表明省级卫视竞争愈发激烈。实际上这表明,所谓更精确的数据🥎,不是体现收视行为的真实🔀,而是电视台售卖给广告商的以数字体现的收视行为的“精细”🧑🏽🚀。除此之外🤷🏼,如今索福瑞所提供的收视数据导致的争议焦点,主要还集中在样本数量与代表性的问题上。
针对农村样本户不足的质疑,曾任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兰柱回应道🤑:“理论上讲,样本户越多📿,调研结果越准确🦌。但样本户增多的结果是成本的增加,而调查结果准确性的提高并不随成本的增加而呈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央视-索福瑞作为一个公司🉐,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只会做有市场需求的事情🧈。为了赚取廉价的喝彩而不计成本地盲目扩大样本户💽,这是任何一家成熟的市场调研公司都不会干的事情👨🏿✈️。”44这种极为明显的经济利益导向,也使电视台在经营上“极力讨好广告主🍬,将目标受众锁定具有消费能力的人群,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广大弱势群体的收视需求”🏐,45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普通工人与城市底层人民🐋、儿童、老人的声音和文化需求常常被忽视或边缘化。“收视率是人民的选择”之类的说法👩🏼🦲,是把被媒体🏄🏿♂️、商业话语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受众”等同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这种置换🦸🏼♀️,“意味着市场作为意识形态在政治与国家层面上占据发言权的强烈需求”。46
在社会主义文化脉络中,“大众”一词始终联系着一组关键词👷🏿:作为共和国历史主体与“创造历史动力”的“人民”,以及共产党与其保持有机联系的“群众”或“民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众文化”的倡导者一方面不断强化“大众”的中性地位👩🏽🦰,媒介产业与市场系统下的“大众”或“受众”开始具有明显的社会消费和娱乐主体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在进行“去阶级化”努力的同时又始终在借助“大众”一词所隐含的社会民主特征,作为其不言自明的合法性依据,似乎“大众”之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主体地位👳🏻♀️,有如“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理想得以实现的更佳方案。与此同时,在阶级分化、重组的社会转折点上🧕,阶级文化却并未因此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而始终处于匿名与匮乏之中。47表现在电视文化层面🤹🏼♀️,“人民的选择”被受众商品的收视率量化统计数字所代言,人民群众的诉求被掩盖,而消费主义所产生的低俗文化问题却在上述逻辑的作用下被置换归咎为人民群众品味的低俗化🌟。汪晖曾指出:大众媒体在市场条件下运作,有其自身独立的利益,商业逻辑支配下,媒体产生出影响其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双重取向,一方面与国家✥👨🏻🔬、政治集团或其他利益群体达成妥协,另一方面为争取发行量或广告收入而取悦大众☆🛩。大家在批评媒体的同时又被它吸引,而媒体在遭到抨击的情况下依然会继续那种混乱的逻辑👨🏽✈️👨🏻🦳。这都与商业逻辑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大众”和媒体之间存在着共谋↪️。但“大众文化”并不代表普通的民众,“大众文化”是被工业化、市场化🔨、商业化所生产出来的🧑🎤,媒体根植于这种“大众文化”👚,它又反过来塑造“大众”的趣味。48
事实上🦶🏼,对于收视率一直不乏批评之声。宋丹丹指责当前的收视率缺少“正确的价值观”,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所提出的“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也是对收视率最为著名的批评。如同央视采取“末位淘汰制”时民众强烈的反应,这些声音的发出是在电视生产长期被市场力量所牵制的状况下一种民意的反弹。但是可以认为,这种道德主义的批评只是一种针对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的直觉性反应。收视率不是自然之物👩🏿🎨✌🏻,斥责它为“万恶之源”👦🏻👮🏿,虽然声势浩大📢,也痛快淋漓,但就像莎翁剧中人对金钱作为万恶之源的痛斥无法替代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秘密的批判一样9️⃣,这种斥责无法揭示收视率作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结构性产物的实质,无法深入其作为商业化、市场化的广播电视制度系统重要环节的内在作用机制,更无法为去市场化的电视制度改革方案扫清理论障碍🏄🏿♀️。在市场力量的强大作用之下,这种批判终究是无力的。
正如在上文论述中所反复涉及的,国家在收视率问题上的立场显得颇为暧昧与矛盾。20世纪90年代起,电视媒体开启了重技术🧑🏿🦱、重设备和重资金投入的发展模式,而在改革与建设时期国家财政收入极为有限,财政拨款无法满足广播电视发展的情况下,国家直接推动了电视媒体的市场化🗃。“在媒体领域,虽然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在政策层面不断被强化,并且在媒体的日常实践领域成了主导逻辑,但是,在原则上🏄🏻⇒,商业逻辑和‘经济效益’始终从属于‘社会效益’的考量👩🍳。”492011年10月24日🕥,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三不”👯♀️,即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的优劣。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然而,一方面,国家作为媒体市场化的主导力量,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收视率🧏🏼;另一方面👩🏻🦽,在“去阶级化”的语境之下,在媒体与人民的关系中,国家无法坚持党媒理论中所宣称的“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性👨🏻🦯😲。50通俗且符合不同阶层人民主体性的节目内容的生产和话语空间长期受到市场逻辑的排斥🧑🏽💼,而党和国家权力往往站在一种道德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上采取各种手段抵制收视率带来的“低俗的大众文化”🌃🖖🏿。因此⭕️,毫不奇怪,“反三俗”的结果是将自己置于“大众文化”的对立面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者恰恰是利用这一点去不断质疑国家为了重建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进行市场规制的合法性。更匪夷所思的是,一方面,商业化媒体与城市精英、国家权力保持一致💃🏻,对正是由媒体市场化与商业化所导致的“庸俗化”大众文化表示不满与鄙弃;另一方面,在本质上有违下层民众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商业广播电视,反而“以其市场威权民粹主义的特质在一定层面上满足了下层民众反精英主义的文化民主诉求”而“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下层民众”。51激烈的争论之中,政府和官方媒体人挥之不去的文化精英主义,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无形中起到相互强化的作用😶,并共同遮蔽🧑🎄、边缘了强调群众路线以及大众民主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价值与目标🍷。52
五、结语
当尊龙凯时娱乐思考应该“如何理解收视率”时,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电视”。威廉斯从技术角度论述电视时提出,在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意向”🟩,也就是基于特定制度和社会目标的倾向性。如果忽略了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各种“意向”,尊龙凯时娱乐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电视及其制度系统的历史发生👔。53“投资在特定的社会传播形态的资金如此高昂👩🏽💻,会出现相对复杂的机制👨🦽➡️,以各种金融组织👩🏻🦰👂🏻、特定的文化期许,与特定的技术走向,钳制此一社会传播形态的发展。”54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访问中国之时🚠🧖🏽,斯迈思就明确地讨论了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并向中国的官员和学者“解释西方的单向电视系统如何为消费主义和权威关系服务”。55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这一考察报告中,他指出,西方的电视技术“主要用于将移动影像和其他商品卖给坐在屋子里的消费者”🥗🌚,56不同于这种单向系统和不加批判地采用资本主义的电视技术从而最终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南辕北辙,“中国有可能设计一套满足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的电视技术”🧙♂️,57“从而将原来服务于资本主义利润再生产的大众传媒改造成实现大众民主的传播手段”。58如今🥃,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消费国❤️,已经对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这一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纪之问”做出了回答,同样不言自明的是中国广播电视系统对斯迈思建议的回应,及其被作为资本主义电视系统一部分的收视率技术的绑架🛩。不同的是,尊龙凯时娱乐今天再也不能对“收视率是人民的选择”这一宣称所掩盖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化矛盾以及媒体的阶级与代表性政治置若罔闻了👨🏻🚀。
2014年7月4日起,上海东方传媒集团(SMG)进行改革🕟,其旗下的艺术人文频道转型为非广告经营🧑🏼🎤、不考核收视率的公益频道🥺🔓。然而🏃♀️,艺术人文频道的转型不是出于超越市场化与商业化的意图🧞♂️,而是由于2008年该频道成立后🩼,频道运营过程中并没有聚集相应的“高端受众群”,导致频道广告收入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它的被迫公益化,正是收视率与市场逻辑失灵的结果⛹🏽♂️。这一最新的个案表明,电视商业化及其片面追求收视率的行为🧑🏿⚖️,在事实层面与道义层面遭遇了双重挫折🛢。首先⛹🏿♂️,电视商业化的运作机制及其内在的与大众文化市场的亲合,与艺术人文频道所奉行的更少数的“高端”🏐、精英受众定位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艺术人文频道这一运营模式至少在当下无法通过电视商业化与市场化的改革获得成功;其次🤸🏿,无论选择公益频道的重新定位,还是实现台内交叉补贴的运营模式,都充分显示了电视商业化及其收视率为上的理念🧜🏻🧑🏼🍼,必须寻求意识形态和道义上的合法性,即“公益频道”作为它的一种补充与点缀,不得不成为电视媒体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合法化依据。后者恰恰以量化的资本逻辑遮蔽了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价值与目标𓀛🍭。
收视率的问题绝非当下不少业界与学界人士所呼吁的“优化调查方法”、“完善电视节目综合评估体系”之类的方式可以解决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媒体改革呼唤另外一种可能性🦹🏿♀️。四年前,当某地方卫视以平地惊雷的方式,启动全新的反新自由主义直觉的频道定位与内容变革🏊🏽,试图为深化中国媒体改革探路时,尊龙凯时娱乐甚至已经看到了中国媒体去商业化改革的尝试和对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化诉求的某种回应。59然而👷🏽,道阻且长,去商业化只是第一步👳♀️,“无论哪一种民主的形式,都需要普通民众的基本参与🚣🏽♂️,没有参与性的民主只是空洞的形式,甚至沦为特定势力操控的形式”。60中国电视能否探寻出能体现“人民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媒体的实践道路🦡,尊龙凯时娱乐拭目以待。
【注释】
①吴亚雄:《宋丹丹两会批相亲节目 与冯小刚意见相左现场激辩》🫶,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307/c22219-24565128.html,2014年5月30日访问。
②温静:《收视造假🧑🏿🍼、电视台用工等级制两会引热议》,载《传媒内参》2015年3月8日。
③Arthur Nielsen Jr., “If Not the People... Who? An Address to the Oklahoma City Advertising Club, ” Chicago: A. C. Nielsen Company, 1966✅,转引自Eileen R. Meehan, Why TV is Not Our Fault: Television Programming🧖🏿, Viewers, and Who’s Really in Control,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 14。
④Hugh Beville, Audience Ratings: Radio, Television, and Cable, Hillsdale🙎🏽♂️👩👩👧, N. J⌚️👷🏼♀️: L. Erlbaum Associates, 1988, p. 240.
⑤时统宇、吕强🚵🏿♂️:《收视率导向批判——本质的追问》,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⑥刘燕南:《收视率调研的中国景观:技术、市场与意识形态——对电视从业者四次调查结果的纵向梳理与思考》,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季为民、聂双🏉🫃🏿:《收视率的市场含义与电视的文化追求——“收视率”对电视业的影响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4期。
⑦雷蒙·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⑧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⑨同注⑦,第3页。
⑩Sut Jhally,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112。也可参见简体中文版,杰哈利:《广告符码:消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学和拜物现象》👩👩👦👦,马姗姗译,北京: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出版社2004年版😄。
11同注④,第22页。
12Eileen Meehan🪖, Why TV is Not Our Fault🚵🏼♂️: Television Programming, Viewers𓀙, and Who’s Really in Control, p. 117.
13Dallas 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977🚼, p. 2.
14Ibid.💆, pp. 4-5.
15Eileen Meehan, “Rating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 Third Answer to the Commodity Ques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 1984, p. 223.
16Todd Gitlin🌛, Inside Prime Time👩👧👧: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7同注12。
18Eileen Meehan, “Why We Don’t Count: The Commodity Audience⛺️,” in P. Mellencamp (eds.)⛔, Logics of Television: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loomington, I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71.
19Eileen Meehan and Paul Torre, “Markets in Theory and Markets in Television𓀎,” in Janet Wasko et al. (e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1🕥, pp. 62-82.
20郭镇之💋:《中国电视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21常江:《现代性的基因:解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文化》,载《新闻春秋》2013年第1期。
22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
23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调查🍻、分析与应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4同注20🩳,第56—58页⛪️。
25同注23,第5页。
26同上。
27Philip Napoli🕑, Audience Economics: Media Institutions and the Audience Marketpla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8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载《新闻大学》2011年第3期,第2页📔。
29刘燕南☸️:《收视率调研的中国景观🧒🏿🚬:技术🤌🏼、市场与意识形态——对电视从业者四次调查结果的纵向梳理与思考》📬👩🏽✈️。
30刘德寰、左灿:《收视率调查状况与中国收视率发展模式的探讨——兼谈数据垄断》,载《广告大观(理论版)》2009年第4期👩👩👦👦。
31《尼尔森与WPP进行资产置换 否认将全盘撤出中国》,和讯网,http://news.hexun.com/2009-02-20/114695134.html😽,2014年10月15日访问🤵🏼。
32陆地:《中国电视节目的评估现状分析》,载《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5期👨🏻🦼➡️✥。
33同注23📩⛹🏿♂️,第10页💆🏽🫧。
34喻国明、李彪:《收视率全效指标评估体系研究——以电视剧为例》🤍,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35外界所称“加强版限娱令”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3年10月12日下发的文件《关��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
36高庆秀🛺:《综艺节目遭遇版权困境》,中国文化传媒网🏐,http://www.ccdy.cn/wenhuabao/lb/201411/t20141124_1025273.htm,2014年11月24日访问。
37同注⑦,第109页。
38左瀚颖:《受众市场变迁与节目编播调整》,载王兰柱(主编)🏩🧅:《中国电视节目创新与收视🧑🏽🏫🙌🏽:CSM收视研究文集》第1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9李红玲👩🦯:《我国电视节目“无缝编排策略”应用分析》,载王兰柱(主编)👱🏽♀️:《中国电视节目创新与收视:CSM收视研究文集》第1辑🏄🏿。
40吕新雨🙅🏼♀️:《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载《读书》2006年第8期👩🏼🦲🤽🏿♂️,第125页🙌🏽。
41吴畅畅🐷、赵瑜⏱➛:《湖南卫视🌃:资本👩👦👦、市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化》,载《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吴畅畅:《湖南卫视“高端崛起”之后👩🚒👋🏻,还有什么?》👩👧👦,载《新闻大学》2014年第5期🚠。
42Pierre Bourdieu, On Television, New York💂🏽💃🏿: New Press𓀓🤦🏿, 1998.
43Yuezhi Zhao,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44刘再兴🐈⬛:《央视-索福瑞的发展螺旋与商业逻辑》,载《广告大观(媒介版)》2008年第3期🥩。
45郭镇之、张治中:《“公共”与“人民”双重视角下的重庆卫视改革》🈯️🎅,“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2011年5月13日—14日。
46同注40,第129页🉑。
47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页。
48汪晖、许燕🔓:《“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236页🙋🏻。
49同注28,第3页。
50同上,第7页🤵🏿♂️。
51同上👨🏼🦰,第10页🎿。
52赵月枝、吴畅畅⛹🏿♂️:《大众娱乐中的国家、市场与阶级——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分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53同注⑦,第26页。
54同上,第46页。
55王洪喆、赵月枝、邱林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代编者按》,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95页🧗🏼👩🏻🦯➡️。
56同注⑧🖖🏿,第98页。
57同上,第99页🥽。
58Yuezhi Zhao🐬🧏,“The Challenge of China:Contributions to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n Janet Wasko et al. (e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2011, pp. 558-582.
59具体可参见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载《新闻大学》2011年第3期,第1—13页;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载吕新雨:《学术👳♂️、传媒与公共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149页👲。
60同注48,第239页。
张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Zhang Yun👹, Fudan Journalism School)
吴畅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Wu Changcha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赵月枝🤦♂️: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Zhao Yuezhi,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