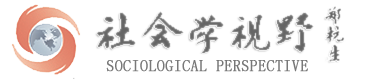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联系电话🕒:010-62511143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
杨振宁
主题: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
嘉宾⛹🏿:杨振宁
主办:中国农业大学《名家论坛》
时间🤵:
编辑🧑🏽🎨:周东旭
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美籍华裔科学家。历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等院士荣衔⬇️。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二人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精彩摘要𓀉:
与同学讨论是深入学习的极好机会。多半同学都认为👨🏿🎤,从讨论得到的比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还要多,因为与同学辩论可以不断追问⚾️,深度不一样。
一个人最好在研究开始的时候,进入一个新领域🦏,就像挖金矿🛑,挖新矿容易出成果🩺🏆,如果一个地方人家已经挖了五年,要想再挖出新矿𓀍,就比较困难。
中国教育哲学讲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的🧑🦲🧑🏽🦰,不知道的,都要想清楚👩🏻🦯➡️,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这种教育哲学♾🧘🏽,有很大好处,也有很大坏处。
一个社会要想科学非常成功,是不是必须制造一种风气🏄🏻♀️,使年轻科学家都很冲,朝中
杨振宁讲座实录⛔️:
少年读到《神秘的宇宙》开启对物理的兴趣
当直觉与书本知识有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必须抓住,把本来的直觉错误想清楚,形成新的直觉
我1929年到清华大学🧝🏼♂️🎥,当时7岁🤞,就读清华大学里的成志小学(编者注:清华附小的前身),我父亲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
4年后进入北京城里的崇德中学,现在叫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在宣武门附近🦿🏌🏻♀️。学校很小👩🏿🦲,差不多300个学生,有一个小图书馆,我喜欢到里面浏览书籍🥷。初中二年级,我在图书馆发现一本翻译过来的书🤹🏻,叫《神秘的宇宙》,描述1905年物理学大革命、1915年相对论和1925年量子力学,这不只是20世纪物理学的大革命,也可说是人类知识历史上非常重大的革命。我当时并不太懂其中的内容🏃,不过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与我后来学习物理有密切关系🏌🏽。
1937年夏天我刚刚读完高一🟥,抗战就开始🧑🏼🦲,尊龙凯时娱乐全家搬回合肥老家🧑🏼🦳。后来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到昆明就职,1938年春天,尊龙凯时娱乐就到了昆明。当时中学生流离失所的很多🫚,教育部就规定不需要有中学毕业文凭也可以参加高考,我当时高二🚈,算便宜一年👱🏽,参加高考就进入了西南联大🧟。
高考考试科目中有物理学🦻🏿,我高中并没有学习物理学,就借了一本标准教科书,关门念了一个月,原来我非常喜欢物理,觉得更合我的口味👈🏿,所以就进入西南联大读物理学,而我起初报考的是化学👨👦。
在大学,教科书说圆周运动是向心的,与我的直觉不一样。思考一两天后,才了解到原来速度向量不单包含量,还有方向🧑🦯,把方向改变加在其中⤵️,圆周均匀加速就变成向心👌。这个教训非常重要,当直觉与书本知识有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必须抓住,把本来的直觉错误想清楚👽,形成新的直觉。这是真正懂得一门学问的基本过程。
吴大猷👳🏼♂️、王竹溪两位师长引领进入研究领域
与同学讨论是深入学习的极好机会👩🏼🍼。多半同学都认为😞,从讨论得到的比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还要多🚗,因为与同学辩论可以不断追问,深度不一样
大学四年级需要写学士论文🧙♀️,我去找
吴大猷把我引到对称与群论领域。我学到群论的美妙和在物理中的深入应用,对后来工作有决定性影响🟫,对称理论是我一生的主要研究领域,占我研究工作的三分之二👩🏻🦱。
1942年我取得学士学位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硕士🏊🏽♀️,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编者注🤼♀️:物理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83年去世)。王先生的专长是统计力学,属于物理学一支👙。统计力学是我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占我一生工作的三分之一👰🏽。
我在研究院的同班同学有黄昆(编者注⚗️: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2005年去世)和张守廉(编者注:著名电机工程专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电机系主任)🤟。我在黄昆70岁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描述当时尊龙凯时娱乐无休止的辩论物理题目🧑💼。记得有一次尊龙凯时娱乐所争论的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从喝茶开始辩论,到晚上回到学校🪖,关灯上床,辩论仍没有停止。现在已经记不清争论的确切细节,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三人(编者注: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蜡烛💂♂️,翻看海森堡的《量子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辩论。
根据我读书和教书得到的经验,与同学讨论是深入学习的极好机会🪡。多半同学都认为,从讨论得到的比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还要多,因为与同学辩论可以不断追问🖨,深度不一样。
求学美国奔着敬重的诺奖得主费米选择芝加哥大学
一个社会要想科学非常成功,是不是必须制造一种风气🙋🏼♀️💇,使年轻科学家都很冲,朝中
1944年我研究生毕业,教了一年中学👩。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印度到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当时中国与美国之间不但没有航班👩👩👧👦,也没有轮船。美国当时在亚洲有几百万士兵👨❤️💋👨,所以美国就造了一些5000吨左右的船,从印度把兵运回美国⏪,每个船中有一二百个舱位留给非美国军人。尊龙凯时娱乐20几个公费留美学生在印度等了两个月👨⚕️,经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最后到达美国纽约。到纽约后我请求进入芝加哥大学。
我在西南联大学的物理学已经相当高深,那时我最佩服3个20世纪重要的物理学家🆓,一个是爱因斯坦(Einstein);一个是狄拉克(Dirac)🪂,英国物理学家;第三个是恩芮科•费米(Enrica Fermi)🏌🏽♀️,意大利出身,37岁时就获得诺贝尔奖🦣。
费米在芝加哥主持建立世界第一个原子反应堆👩👦👦,他是第一流的实验物理学家🤙🏼,也是第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事实上🏋️♂️,物理学家在19世纪以前是理论与实验都要做的,牛顿既研究理论又做实验,可到20世纪,理论与实验变得更复杂,很少有人能够两方面兼做。20世纪能够在两方面都做出第一流工作的物理学家就是费米🏦。
去美国的路上👦🏽,我就想好跟着
1946年初我到芝加哥大学👷♀️,开学后就上了费米的课🏒,很快熟起来。我提出跟着他做实验论文,他研究了一下说不行🤹🏿,因为他的实验不在芝加哥大学,而是在40公里以外的一个实验室🦹♂️,当时是保密的,所以我就没做他的研究生🦉。
2001年是费米诞辰一百年,我在庆祝会中做演讲。我说🔁,费米是20世纪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中最受尊重和崇拜的人之一🤦🏻♀️➛,他之所以受到尊敬和崇拜,是因为他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两方面的贡献,是因为他领导下的工作为人类发现了强大的新能源🦹🏻♂️,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个性👩🎤。他永远可靠和可信,永远脚踏实地,他的能力极强😯,却不滥用,也不哗众取宠,也不小瞧别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
一般来讲🏃🏻♀️➡️,美国重要的科学家比较冲🦐,同时👈🏿✌🏻,美国科学又是非常成功的。所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一个社会要想科学非常成功,是不是必须制造一种风气,使年轻科学家都很冲🧗♂️,朝中
感受中西教学方法差异
中国教育哲学讲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的,不知道的🏰,都要想清楚,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这种教育哲学,有很大好处,也有很大坏处
在物理学习方法上,芝加哥大学与国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国内是推演法,在书上学到一个理论👨🏿🎓🗻,按定律推演到现象。芝加哥大学正好相反,不是从理论而是从新的现象开始,老师和同学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这些新现象💌,能不能归纳成一些理论🧔。如果归纳出来的理论与既有理论吻合,那很好,就写一篇文章👯♂️;如果与既有理论不符合,那更好,因为那就代表既有理论可能不对🦡,需要修改。
整个气氛与国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中国使用推演法,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根基;到美国🧴🏊🏿♂️,学会多注意新现象🛍,由新现象归纳出理论✪。
中国教育哲学讲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就是说你得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与不知道的东西分清楚,不能够乱七八糟🧑💻。有些东西你是知道的,有些东西你不知道🫴🏼,都要想得清清楚楚🏊🏿👬,这个才是真正的学习。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很重要➝,有很大好处🔅🐮。
可是这种教育哲学也有很大坏处🐻🌶,事实上有许多知识不是这样学来的,比如一个小孩学讲话,并不是按部就班,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学会💆🏼,他在一个不太清楚的时候,就弄出来😁。关于这一点🍸,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渗透性学法✋🏼,渗透性学法是中国传统不喜欢的。
事实上,很多东西第一次听不懂,第二次再听👼🏻,还是不懂,可是就比第一次多懂了一点,等听到很多次以后👳🏿,就忽然一下子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与西方教育哲学一个很大区别🪛。我上学时就觉得西方学生没有把东西想清楚的习惯⛈,可这并不阻止他们做出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非常聪明的年轻人,用渗透方法吸取知识的能力很强。
芝加哥大学当时是非常成功的,研究气氛浓厚,有很多讨论会,多注重新现象🕖,新方法,少注重书本上的知识。1948-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有4位获得诺贝尔奖,这与当时浓厚的学习气氛密切相关⚠。
1971年我到中国参观访问,中国大学的课程是非常之深,有所谓“四大力学”(编者注:传统的《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统计物理》组成)📉,每一名物理系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这四门理论课。四大力学当然重要,没人能否认它们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研究方向在“希望破灭”中清晰
一个人最好在研究开始的时候,进入一个新领域,到一个旧领域当然也可以👇🏽,可是就像挖金矿一样,挖新矿容易出成果🐫,如果一个地方人家已经挖了五年,要想再挖出新矿🔳,就比较困难
1946年上半年🙍🏽♂️,经过费米推荐,我成为泰勒(E•Teller🧑🏽🎨,编者注:出生于匈牙利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2003年去世)的研究生。泰勒给我一个研究题目,几个星期以后,我给他看计算结果👓,泰勒觉得很好👰🏼♂️,还安排我做一个报告🧑🏿🔧,大家的反应都非常好🥃。泰勒说可以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可我觉得还不够好,总没写出来🍜。
1946年秋天费米介绍我跟着艾里逊(Allison)教授做核物理实验🏄🏼。我在实验室做了差不多20个月的研究工作。1947年我曾经写信给黄昆🧑🏿⚖️,他那时候在英国读研究生🔅,我的信中用了“希望破灭”。因为我在艾里逊实验室做得不成功,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我这人天生不是做实验物理的🧙,动手不行,常常在实验闯祸,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回想起来🧳,那一年我自己找了四个理论题目,第一个是昂萨格(Onsager,编者注:美国物理化学家,1976年去世)关于伊辛模型(Ising Model)的文章,这是当时有名的统计力学题目🛤。第二个是布洛赫(Felix Bloch,编者注👨🏻:瑞士物理学家🗣,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关于自旋波(Spin Wave)的文章,也是有名的统计力学题目。第三个题目是规范不变。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发展方向,但弄了几个礼拜无果而终。研究中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所有研究生差不多都有过一些沮丧。不过大家不要因为沮丧就觉得没有希望,不是你一个人,所有研究生都有这个问题。
前三个题目做来做去都没有结果,第四个题目是核反应中的角分布问题。这一问题与对称有密切关系,我就想到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半时间,自己找了四个题目,只有第四个有所发展,前三个费很大劲👩🏻🎤,没有结果。第四个题目是关于群论的🙇🏼♀️🤹♂️,走到这个领域我非常兴奋,因为那时很少人对把“对称”用在核物理中感兴趣👨👧👧🧚🏿,我走进去了,所以很快占领一个新的领域🔭🧏♀️。
我因此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一个人最好在研究开始的时候🕝,进入一个新领域,到一个旧领域当然也可以👨👨👦,可是就像挖金矿一样,挖新矿容易出成果👩🏿🚒,如果一个地方人家已经挖了五年,要想再挖出新矿🤷🏿,就比较困难🧑🏻💼。
我在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就是与邓稼先的交往。邓稼先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低两班,后来在西南联大,他也是物理系🤞🏽,因为我跳了一级,所以他比我低了三班🫚。我到美国后📧🤰🏿,没过几年他也来普渡大学读书🙅🏼♂️。1949年夏天他从普渡大学到芝加哥,我与他、还有我弟弟租了一个公寓📰,住在一起。他第二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50年代带领28个刚刚获得学士学位的物理系年轻学生研究制造原子弹🦶🏽🧝♀️,对中国原子弹和氢弹发展作出绝对性贡献,成为“两弹元勋”🧑🏼💼。
为爱留在普林斯顿 开始学术最有成果的17年
我认为所有研究工作多多少少要经过三步曲:兴趣--准备工作--新的突破点
1948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留校教书。1949年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当时最红的理论物理题目是“重整化”,在普林斯顿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要去普林斯顿🕧。
本来想在普林斯顿呆一年就回芝加哥大学,但在普林斯顿碰见了我以前高中教过的学生(编者注🧁:杨振宁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
普林斯顿的研究所不大,没有学生🦓,大概有20个教授,四五个研究领域,一二百个博士后和访问学者,是一个纯研究性的象牙之塔,非常成功。
我到研究所的时候🚴🏼♀️,那里大师云集。爱因斯坦刚刚退休😼,尊龙凯时娱乐年轻人没有人去骚扰,都很尊敬他🏡。有一天我带着大儿子在路上看见他🦵🏽,就照了一张照片🧝🏿🤽🏼♂️,我自己从来没有与爱因斯坦合过照🧎🏻♀️。
在研究所是完全放任的政策,每个人的消息都很灵通,自己找自己的合作者,这种方式到现在已经维持了七八十年,非常成功🐩。我在研究所的主要兴趣是核物理🌻。
1949年11月初的一天💽,在往返于普林斯顿大学与研究所之间的街车上🧚🏻♂️,Luttinger(编者注🚴🏿:研究所的一名博士后)偶尔和我谈及伊辛模型,Luttinger说😋,考夫曼(Bruria Kaufman👳🏼♀️👩❤️👨,编者注:女物理学家🧑🦰𓀁,昂萨格的学生)已经把昂萨格的方法简化,因而可以通过2n个一系列“反厄米特矩阵”搞清楚。我对这种表象了解得很多,所以很快就理解了“昂萨格-考夫曼”方法。一回到研究所,我就搁置原来的工作👲,根据我在1947年关于这一问题的经验,再加上新的元素和观念,一两个小时后就完全弄明白↗️,推导出“昂萨格-考夫曼”解法的基本步骤🤸🏋🏿♂️。
我觉得昂萨格还没有做完💱🈹,于是就继续算下去,并得到最终公式。这份成果发表后,物理学界很多人非常注意我🧘,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因为我把一个很复杂的计算变成很简单的公式,在芝加哥大学自己找的第一个题目开花结果🚶🏻♀️➡️。
此次研究的经验是什么呢?研究是一个三步曲:第一步是兴趣🦍,我跟
我在芝加哥大学感兴趣的另一个题目是“规范不变”。1953到1954年我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访问,同办公室一位年轻人米尔斯(Robert Mills)谈话🔠,很自然讲起来我对“规范不变”的不成功研究,尊龙凯时娱乐讨论两天以后,决定再加两项进行运算🫴🧑🏿🎤,结果越算越简单。尊龙凯时娱乐知道挖到宝藏了!
我把运算结果写成一篇文章寄给《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变成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它把电磁学结构很美妙的进行了推广🤞🏿。电磁学结构是物理的一个中心🏡,今天所有手机💁🏼♀️、电视、无线电都要用这个方程式。1954年文章发表后,并没有被大家注意,后来学者引进“对称破缺”观点,才大大发展了这一问题𓀇👨🏽🦲,成为标准模型。
通过这件事我又得到一个教训,物理学中的难题往往不能一举完全解决,如果把其中一部分解决,很可能为最后解决办法提供重要的中间一环🎚。另外,与别人讨论往往是十分有用的研究方法👩💼👨🏼🏫。
1955到1956年我转而研究另外一个问题,θ与τ。θ是当时发现的衰变成2个π的粒子🙁,τ是另外一个粒子,衰变成3个π✋🏿。一方面发现θ跟τ有同样的质量、寿命,而通常2个不同粒子的质量比差很多,几倍、几十倍甚至几千倍🔵。所以这两个粒子可能根本就是一个粒子🪫,粒子有时候变成2个π♒️,有时候变成3个π,同一东西变成两种不同的是常有现象👩🏽🎤。可是,另外一方面,存在宇称守恒定律🧙🏿♂️,θ与τ不可能是同一个离子,因为根据此定律,2个π的“宇称”是+1,而3个π的“宇称”是-1💇🏼♂️,如果θ与τ是同一粒子🤌🏻,那么它既能衰变成+1的宇称,又能衰变成-1的宇称👩🏿,宇称就不守恒了,违反了基本原理。当时就分成两派,一派说θ与τ是一回事👌🏻,一派说θ与τ绝对不可能是一回事,当时很多文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与实验都没有能够成功😮💨。
1956年夏天我和李政道合作,检查宇称是不是真正守恒,做了3个星期的多种计算后➛,尊龙凯时娱乐很惊讶地发现👩🍼,所有过去的β衰变试验中并没有任何宇称绝对守恒的根据。好几百个β衰变试验一致认为证明了宇称守恒,但这些结论都是不对的🥠,尊龙凯时娱乐从而提出怎么样做实验能够测定β衰变中宇称不守恒🚕。这些实验比以前实验要稍微复杂一点☸️,提出来以后学生都不肯做,第一,这些实验都不简单,他们说不值得去做;第二,没有人相信宇称是不守恒的🛃。
只有吴健雄(编者注👨🏿✈️:美籍华裔女物理学家,有“
1997年吴健雄去世😘,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吴健雄的工作以精准著称于世,但是她的成功还有更重要的原因📁:1956年大家不肯做测试宇称守恒的实验,为什么她肯去做此困难的工作呢👳🏽?因为她独具慧眼🧜,认为宇称守恒即使不被推翻🔝,此一基本定律也应被测试🎦🦹🏻♀️。这是她过人之处。”吴健雄自己曾说,永远不要把所谓不言自明的定律视为必然🕞。
1949年到1966年是我一生研究工作最有成果的17年。1966年我离开普林斯顿,离开这样一个象牙之塔是极不容易的决定◼️,后来常常有人问我,后不后悔离开🤏🏼,我后来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是新创建的大学,帮助一所新的大学变成一个好的研究性大学是一件很有意义事情,可以说这是我的一个重要转折。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基本上就是把我过去的研究经历归纳一下🧑🏼🌾,得出一些结论🙆♀️,也许这些结论对在座的年轻人会有些用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