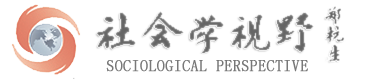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
杨念群
原文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06期
一🟠、“宗族”、“庙宇”与区域社会史研究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现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史和政治史占据着绝对垄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和政治史是描述社会经济形态总体演变趋势的工具,虽然“中国经济史”中间往往加上“社会”二字👨🏼🎨,叫“中国社会经济史”,实际上在传统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框架内,是看不到什么“社会”的影子的💆。因为中国历史的变迁图景只容纳了生产力变迁下一种粗线条的人际阶级关系的变迁,而不会给社会意义上的变化留下什么位置。
80年代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界率先提出了“社会变迁”的问题,力求突破从“生产形态”的角度理解历史演变的旧路子🧘,用新的描述取代老的分析,如用“社会分层”取代“阶级分析”,用“结构-功能”框架取代“社会发展阶段论”。这种替代式研究因为区别于传统经济史的陈旧语汇和公式化的论证方式,一度风靡史学界。这种治史风格也比较吻合于80年代整个思想界的阐释风格,即喜欢从大处着眼,搞超大范围的中西比较和框架分析👮,诠释单位也往往着眼于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这两个系统的作用中,“社会”仍屈从于宏大叙事的压迫而没有什么机会进行细节的展现。
真正把“社会”当做一种分析单位,而不是屈从于“结构”束缚和成为现代化演变分析的附庸是从90年代开始的🧖🏽♂️。90年代的中国史界开始注意把历史演变不仅仅看做是个时间因果序列的问题,而且也是“空间”转换的问题。也就是说,仅仅以“中国”为研究单位🪻,其实研究的只是一个“政治”与“制度”的实体,探讨这个实体的运作固然重要,却难以发现基层社会的运行状态。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新的研究空间,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社会”。在西方史学界,“社会”是与“国家”相对抗的一种空间,它被理解为一种区别于上层世界的“公共领域”👩🏻🦽➡️。可“公共领域”又往往被理解为是在城市中出现的,与“市民社会”的出现相匹配👳🏽♀️。所以🛁👨🏼🍳,“公共领域”被引进中国时,由于缺乏西方的历史情境🏐,在应用到中国历史分析时少有成功的例子💁🏿。相反,由于中国人口以农为生者占绝大多数✤🚣🏻♀️,因此🚶,把乡土中国中的“村落”定位为“社会”研究对象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中国乡土社区的基础单位是村落👯,村落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空间,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吴文藻和费孝通主张👩🎨,以一个村做研究中心来考察宗教的皈依以及其他种种社会联系👩🏼🦱,进而观察这种种社会关系如何互相影响、如何综合,以决定这社区的合作生活。从这研究中心循着亲属系统🧼、经济往来、社会合作等路线🃏,推广尊龙凯时娱乐的研究范围到邻近村落以及市镇[1]🚠。费孝通对“村落”的定位实际上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找到了一个相当合适的研究单位,对以后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导向作用。同时,对“村落”中“宗族”的研究被认为是村落研究的“戏眼”,拥有核心的地位。这取决于一种假设🪦,即村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都是以“宗族”为主导而展开和进行的。“宗族”的存在和凝聚力成为乡土中国能够组成一种“社会”的核心理由。以“宗族”为核心编织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的图景🧙🏻♂️,当然有它的充分依据⛹️♀️,“宗族”在宋明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南方具有支配力的乡村社会组织💹,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宗族”也被理解为在地方社会中解决法律纠纷的最大单位[2]。问题在于,“宗族”理论之所以成立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之上的,即“宗族”的存在恰恰是与集权政治保持距离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在远离政治中心控制的情况下才有广泛生存的可能。因为“宗族”产生时,在基层社会中所具有的自治作用,恰恰是其远离正统统治模式后造成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宗族”的分布必然有其“区域性”的特征乃至限制,而不可能是均质的🤦🏻♂️,好像中国的乡村社会到处无一例外地都被“宗族”所控制似的。既然“宗族”不可能在全部乡村社会中起绝对主导作用,那么🏄🏻♂️👳♂️,以“宗族”为核心的研究就有修正的必要。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另一个“核心词”是“庙宇”。“庙宇”进入社会史的视野👐🏻👩🔬,是因为受到了人类学“象征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仅仅从“村庄”和“宗族”这样的角度切入某个区域进行分析,具有太多的“功能论”色彩🤱🏿,好像农民的生活节奏完全是受一种极端实用和功利的逻辑所支配🧑🏻⚕️,比如受某种纯粹的“生活需要”的支配💴。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尽管农村的生活场景有可能是受某种特定的需要关系所控制,但从文化的角度看♛,仍有可能超越一定的功利目的具有某种较为纯粹的“精神气质”。“庙宇”就是凝聚这种“精神气质”的最佳场所,它有可能透露的正是农民生活世界中不受功利准则支配的那一部分图景。
“庙宇”象征着中国农民具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这好像是个很诱人的看法。可一旦落实到研究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很难在具体的分析中区分“精神”与“功能”两个层次👩🏻🚒,原因就是中国与西方的最大区别乃在于✊🏽,中国农村中的信仰很难像西方那样可以轻易地定位为“宗教”👨🏽🚀。“庙宇”在村落中基本不会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宗教空间,或具有什么纯粹的“宗教”意义👩🏼🦰,它更多地起着凝聚社区世俗活动的作用。道理很简单,中国人本身的信仰系统特别是“民间信仰”系统仍是被相当功利的原则所支配🧗🫑,一般都会服务于“求子”、“求财”的功利性目的🧉。故此,有人指称🚱,中国根本没有“信仰”📝,只有“迷信”,即中国基层的拜神、拜偶像均是以功利的心理为信奉基础的。所以🦹🏻♀️,中国乡村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以独立支撑纯粹宗教信仰的空间🥮,即使在形式上有可能发现某种相似的空间,也往往与村落的生活需求密不可分🦻🏽。这样一来,“庙宇”很可能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差异极大💪🏽👸,在一些地区起核心作用👳🏻♂️,换个地方其作用又可能极其微弱。所以🧝🏻♂️,单纯挪用西方的“表演理论”来单独地寻求“庙宇”的文化象征意义🌥,效果自然是相当有限的🛴。
中国社会史研究自从实现了“区域转向”之后,形成了多元并存的发展局面👩🏻🔧😱,出现了诸如“华北模式”、“关中模式”🐵、“江南模式”、“岭南模式”等流派。虽然这些“模式”所包涵的内容并非十分明晰,也不能说已系统地提出了区别于以往理论的完整表述,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本上是以“村落”为单位🐸,以“宗族”、“庙宇”为核心论题展开论述的,虽有个别的观点是从市场网络、经济变迁和城乡关系等方向力图区别于“村落取向”𓀒。由于区域社会史找到了“宗族”和“庙宇”两个可以从组织与象征层面把握乡土社会的工具,所以,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变成了“区域社会史”研究🏂🏽,而“区域社会史”研究又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
二🤷🏿、从“地方性知识”到“地方感”
“地方性知识”一度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另一种表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地方性知识”其实是“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一种表述👵🏽,是用以对抗“全球化逻辑”的一种工具和武器,只不过这种趋向由人类学家吉尔兹加以放大了而已[3]。
“地方性知识”强调“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来自人类学对“族内人”(insider)和“外来者”(outsider)如何分别看待他们的思维和解释立场及话语表达的问题,有学者概括为“emic/etic”。Emic是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代表着内部的世界观乃至其超自然的感知方式🚰,是内部的描写🚓,亦是内部知识体系的传承者。Etic则代表着一种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这种划分合理与否另当别论😳,但其中隐含的悖论却是相当明显的:他何以在成为一个研究对象本身的“文化”体悟者的同时🙎🏼,又能跳出其限定给予一种“超在地性”的解释?
吉尔兹引用“贴近感知经验”和“遥距感知经验”两个心理分析概念来概括这个困境。囿于贴近感知经验的概念会使文化人类学研究者湮没在眼前的琐细现象中👱♂️,且同样易于使他们纠缠于俗务而忽略实质;但局限于遥距感知经验的学者也容易流于术语的抽象和艰涩而使人不得其要领🦵🏼。吉尔兹的设想是:人类学家应该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的诠释。“它既不应完全沉湎于文化持有者的心境和理解,把他的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巫师写得那样,又不能像请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去鉴别音色似的✹,把一部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几何学家写的那样”[4]。关键在于🏄🏼♀️,这个“度”在哪里呢?
上个世纪80年代,柯文在他那本风靡一时的著作中提到了“移情”的问题,意思是美国汉学家往往为美国的既得利益设置诠释中国的框架🤱🏻,为了避免这个弊端😉,应该改弦易辙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原来出于政治目的构建的中国图像。可是柯文的框架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何以知晓自己的视角是否真正从中国本身出发了呢🙄?这个“中国视角”的标准是什么🤳?柯文提出的方法也不外乎“注重下层”、“横向切剖”的区域社会史视角。这个视角其实与是否是“中国的”没有太多的关系,而仍是国际社会史趋向塑造的一个结果🫚。如果说真有什么联系的话,也是与30年代中国尊龙凯时AG家提出的“乡绅理论”中所倡导的“地方社会”应具有自主性等观点有暗合之处。就笔者的认知来说,真正的“移情”是培养一种与本地情境相认同的“地方感觉”,而不是急于把这种感觉归纳为一种系统知识。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