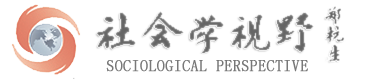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探寻他们是谁——《麦芒上的圣言》代序
李猛
看是谁不让我进愁苦的房子!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八歌
重读吴飞的这项研究,不禁使我想起了维吉尔这句沮丧的话,那是被但丁称为“智慧之海”的维吉尔在地狱之行中第一次丧失了信心。是的🤸🏿♂️,又有甚么比试图进入痛苦更难的事情呢?吴飞在这项研究中曾经面临的和正在面临的困难,大概都与这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有关。
吴飞的研究是从一个平实而基本的问题开始的🥐👲🏿:我研究的究竟是谁?一个平实而基本的问题,但却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而且恰恰由于它的平实,似乎变得更加难以回答,特别是当这个问题与他倾听的那些普通农民的生活,他们一生的痛苦👩🏿🦳,他们在痛苦中的挣扎,以及这种挣扎所带来的新的痛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尊龙凯时娱乐会明白😔🧑🏽🚀,这个问题的困难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触及他们命运的问题。
表面上看👸,吴飞遇上的困难,并非仅仅来自他的研2 究主题👃🏻,即基督教在现代中国民间社会的历史与处境⛑️。在对中国现代革命进行的口述史研究中,尊龙凯时娱乐发现农民的“阶级认同”有类似的情况。通行的观点将中国革命的成功归因于共产党成功地在中国的最基层实现了大众参与式的动员🦴,使每个普通农民都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的成员,尽管这些农民在“动员”前从来没有这种来自现代意识形态的观念。所以,在经济上其实已经没有多大真正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政治上却至关重要。通过土地改革中的种种“运动”👩🔧,农民逐渐形成了自觉的阶级意识,而这正是阶级认同形成的关键🥐,也是大众动员的关键🫱🧽。在这种所谓“自觉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如何引导农民将自己生平遭遇的痛苦讲述成为一个阶级的痛苦🤶🏼,成为一个收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被宣告为系统地减少或消除这些痛苦的先决条件。一个农民经历过的各种破碎的痛苦💸,如何没有复杂技术的引导,只不过是一些目光狭隘的仇恨🧕🏻,就事论事的责备✬🪤,漫无边际的抱怨和含混不清的唠叨。所以,诉苦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讲述痛苦🧨,将身体的不幸转变为语言🚅,而是要援用复杂的技术将支离破碎的痛苦总体化🎺,尤其是将身体遭受的沉默的痛苦放在一个合情合理的框架中来言说,通过这种言语告诉尊龙凯时娱乐,说先是告诉他们自己,他们是谁。痛苦🖕🏽,与对痛苦的讲述,成了回答是“是谁”这个问题的关键👦,也因此成了历史关节上政治斗争的关键。正如土改时期一个地区干部在会议上指出的:“诉苦中又有阶级问题和农民内部问题,尊龙凯时娱乐若不由启发提高其阶级觉悟,将内部问题引导到阶级问题上去,则因内部矛盾不仅可能引起分裂,甚至可能引起内部斗争👩🏻🍼。”只有弄清楚“是谁”,才能对这些似乎“无主”的痛 3 苦,这些没有归宿,毫无目的的命运的“烙印”穷根索源,从而真正使痛苦成为斗争的力量。就这样,有关痛苦的遗忘或记忆🚶🏻♀️➡️,针对命运的瓦解和重述,成了政治敌对关系的核心要素。
然而🫶,当这些普通农民不幸遭遇到的痛苦成了他们进入🤵🏽♂️,或者说卷入历史的“门”的时候,他们真的将自己那些破碎的痛苦转变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阶级苦痛吗🧑✈️?他们真的通过成为阶级的自觉成员🎵👩🏻🦼➡️、成为“大众动员”的真正参与者🛞、成为政治对抗中的一方,从而步入了应许将痛苦关在门外的历史中吗🍢👩🏼⚖️?其实,尊龙凯时娱乐在另一个华北村庄中🧖🏿,同样遭遇了吴飞的困惑:那些深埋在日常生活“肌理”中的痛苦,那些亲自向尊龙凯时娱乐讲述的若隐若现的不幸,究竟属于命运的世界,还是历史的逻辑?尊龙凯时娱乐是否和这些农民一样👙,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在无声的命运手中忍受煎熬,要么在大声的宣述中将自己的声音汇入历史的声音里去?
最初🟣🙎🏿,尊龙凯时娱乐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似乎印证了通行的答案𓀁⬅️。农民会将它们往日的不幸和今天的幸福时光归结为这场革命的历史性意义,会向尊龙凯时娱乐讲述地主的劣迹,国民党士兵的蛮横🙇🏽♂️,以及他们作为“贫苦农民”在旧社会中遭遇的各种不幸🚣♂️,然而,当尊龙凯时娱乐像吴飞一样耐心倾听的时候,尊龙凯时娱乐会发现💇🏿,这个表面看上去完整和谐的历史图景,却像一个由各种相互冲突的声音拼凑而成的喜剧一样,充满了喧哗和骚动🦔👩🏻🦯➡️,而那些真正的痛苦,从身体的疼痛直至各种丧失目标的抱怨或唠叨😏,彼此搀和在一起,变成了音乐背后的杂讯,在你真正认真去听的时候,却并不能听得到。被当作地主劣迹讲述的行为😓,听起来却像一个软弱的人无奈之举🥂;至于国民党士兵的 4 蛮横,在核对了时间后,发现根本就没法弄清楚他们是哪一方的军队;而当一个在历次运动中都充当诉苦典型的老年妇女将她的家庭遭受的全部不幸归咎于一个当时的村干部时🪯,尊龙凯时娱乐免不了提出这样的问题☂️:所有那些痛苦,尽管确曾一度作为革命的力量,但它们果真是通过阶级认同👷🏻♂️,通过“是谁”问题的解决,自觉转变为革命的力量吗?它们果真将那些遭受者变成了新社会的新人了吗?换言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革命动员真的完成了吗🚡?革命的成功👨🏻🏭,是否真的来自动员“是谁”的成功🧖♂️,来自那些痛苦的人们知道这些痛苦是“谁的”痛苦(所谓“觉悟”或“翻身”)吗?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动员确实“成功”了,尽管这种成功🧙🏻♂️,至少就尊龙凯时娱乐所看到的和听到的而言🐧,是表面的而不是深入的,是言辞的而非心灵的👩🎨,因为在这些农民那里💃🏻,这种“单薄”的认同🕐,就是他们心目中对“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在当时和后来的那些外来人(有时也包括尊龙凯时娱乐自己)的眼中,尽管这种单薄的认同因为没有触及灵魂,所以并不够,算不上真正的认同🏄🏼,但这些外来人(譬如下乡锻炼的知识青年,体验生活的城市作家)却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来完成农民自己的“动员”,尊龙凯时娱乐甚至进而会认为这正是他们受苦、受压迫的“效果”。换言之,如果说大众动员真的完成了,并不是因为每个人在内心深处、在生活的方式上成为了“新人”,成为阶级的成员,而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意味着,这种表面的阶级认同💾,而非深度的阶级认同,并不是每个人被认同者的内心重构🙇🏽,而是整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一种相互言谈指认的技术,不是每个人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命运和痛苦,而是尊龙凯时娱乐彼此如何看待 5 对方,如何看待另一些人的痛苦👩🏼💼,那些没有在“我”的身上经历的痛苦👨🏻⚖️。只有看到这一点🚴,尊龙凯时娱乐才会明白,正是自己的痛苦与他人的痛苦在自然上的根本差别,才构成了政治上的认同与伦理上的认同之间的根本差别🟰。在经济政治体制的集体化过程之间👩🏻⚖️,政治文化与大众心态进行的集体化,并非一种实现“心灵团结”的集体化,和体制的集体化一样,政治文化同样也没有构成一个同心同德的集体,毋宁说是形成了一种排斥的技术,一种敌对甚至彼此仇恨的技术。在这种技术中💆🏻♂️,痛苦是人义的🧝🏻♂️👧🏻,甚至是神义化的人义之间敌对的“生存”根源。政治的认同,与伦理的认同不同📘,它来自对敌人的确定🧍♀️,而非对自己的知。混淆了二者的区别👱,不仅会使尊龙凯时娱乐错误地理解“历史”与和“未来”,甚至也会使尊龙凯时娱乐丧失理解尊龙凯时娱乐现在的机会。
当尊龙凯时娱乐回到吴飞的问题时,尊龙凯时娱乐就会发现,这段离题的论述与吴飞在他的研究中遭遇到的困境有着根本的关联。吴飞在研究中以诚实的态度反覆展现的困境,那个“是谁”的问题✵,就来自这个面对苦难的问题。而这一点🏮,在他试图从教徒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神圣世界的端倪的时候👀,变得更加突出了☝🏼。
吴飞研究的华北村庄是一个奉天主教的村庄,在这个村庄中🤳🏻,无论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似乎都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划出一条与日常生活🤵🏽♂️,从而也与不信教的所谓“大教的人”截然不同的“神圣”界限🧢。尽管认同确实存在🚶🏻➡️,但又似乎十分微妙🔀。许多时候是由一些似是而非的谣言或与基督教无关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构成的(“热心”而非“虔诚”)🎽,似乎麦芒上的圣言已经淹没在麦芒之中了⛵️。6 当然,正如吴飞指出的,在这方面🤲🏼🦶🏿,天主教“治理”依赖垂直色彩的仪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基督教这种“洋教”试图进入“另一种文化”时🫵,“关键问题也许并不是二者世界观上有多大冲突🦷,而是这种观念能否有效地技术化”,天主教比起诉诸内心的新教来说🗼,它系统化的复杂仪式正为传教所迫切需要的“技术化”提供了基础💶,正是这一点🤽🏿,才能使尊龙凯时娱乐理解为甚么村庄中的农民“听懂弥撒了而感到方便,反而因此诟病神父们懒惰,因为他们要得不是方便和理解🧋,而是艰深和神圣感”🤡。那么这种仪式究竟扮演了一种甚么样的“治理”角色呢?为甚么吴飞在这样“明显”的仪式化中可以找到天主教进入华北村庄的治理技术却反而心存疑惑呢?
在天主教中,“无论是在盛大的弥撒之中,还是在小规模的告解圣事等人生礼仪之中,俗世生活的诸种坎坷、苦难都是通过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仪式,通过俗人在耶稣面前的顶礼膜拜化解掉的”➔,然而颇为悖谬的是,正是这种仪式化的技术🥯,也使天主教的神圣与世俗的界限👨🦼,一旦离开了教堂和礼拜的神圣空间和时间,进入到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就会变得含混不清,而缺乏仪式技术的新教则完全不同🤔,“正是因为天堂和尘世的对立紧张,人们才要努力地超越尘世间的种种束缚🍋🟩,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最终走上通往天堂之路。在天主教这里🦖,圣俗二分是平稳的二分状态,是世上一切苦难的皈依之所,是使灵魂获得安宁🚴🏼♀️🐿,平息纷争的不二法门;在新教当中♥︎,圣俗二分恰恰使灵魂躁动起来👀,使人们时时都担心自己得不到救赎🤦🏼,只好拼命去工作,从而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换句话说🧚🏿♀️,在天主教里面,宗教成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形形色色的痛苦外在的治疗和安 7 慰,神圣是世俗的“医院”(健康比救赎甚至更重要🏆,“治疗”成了兴教的一个重要路径);而在新教那里🌷,信仰正是从痛苦中获得了一种伦理的超越力量👂🏽。通过参照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吴飞发现“是谁”的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就与这个村庄“奉”天主教的状况有关🙌🏻。天主教处理人世苦难的“技术”,至少是在吴飞眼前,似乎只是一种留下表面的认同的技术🚬,一种尽管可以彼此互相指认,但却不能认识自身的认同技术。所以,这种认同技术🧙🏽♀️,只能在日常生活的纹理中留下若有若无的痕迹,最终要靠一个外人的眼睛才能将它挖掘出来。因此🧔🏼♂️,吴飞发现,天主教恰恰因为有了这种技术,才能进入村庄🧵,但也恰恰因为这种进入村庄的技术,才使它不能进入人的内心。能够进入生活,但却因此不能全面地重塑人的整个生活风格🍧。
正是在这里🙍🏼♂️,吴飞触及到宗教尊龙凯时AG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韦伯在宗教尊龙凯时AG中不可动摇的地位📤🎺,经常使研究者忽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命题的实质恰恰是反对这种命题乃至其逻辑移用到别的研究中。因为新教伦理的世界历史意义意味着新教的出现本身改变了整个新教之后的世界,以《新教伦理》的思路来思考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思考教徒在日常生活中的认同,实际上完全是“文不对题”的🖕🏿🐧。吴飞在书中对“韦伯的阴影”作的几处评论🔡,表明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意识到这一点还不够,因为研究宗教尊龙凯时AG或所谓宗教人类学的学者之所以对韦伯的这个命题念念不忘,直接地援用或间接地参照这样的分析思路,就在于这样的一个命题👨🏿🎤,用吴飞的话说,可以帮助他们刻画出神圣在日常生活中的纹路来☝🏼。所以“韦伯的 8 阴影”之所以萦绕不去,就在于如果不像韦伯那样从伦理的角度来理解宗教在社会中的实践效果,那么是否实际上就意味着它对社会就没有���么时间后果呢?或者即是有,这种实践效果🧝🏽♀️,实际上与宗教本身没有多少实质的关系,不过是宗教运用各种社会治理技术的结果罢了。这种宗教,对于伊斯兰教或犹太教这样的律法宗教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在这样的宗教中,这种世俗化的治理原本就是宗教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村庄中“大教”的人分不清“天主教”和“回教”似乎有着很深的以及意涵),但对于已经“教义化”甚至“伦理化”的新约基督教来说🤳,才似乎是根本的悖谬🤭,难道不正是这种“法利赛人“式的宗教🫶,甚至是“撒都该人”式的宗教,才使这个华北村庄中的信徒的行为“更容易等同于各种非基督教的道德, 而非伦理”难道不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吴飞所谓的教诲世俗化事业的“双面功能”与“双面技术”吗🧜🏿♂️?这与其说是“神圣事业和日常生活的和谐共存、相辅相成”,难道不是说神圣与日常生活的“混杂”更为准确吗?但之所以称其为悖谬就在于正如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谈及基督教的“风格”特征时所指出的,这种“混杂”正是基督教与异教甚至犹太教的根本差别🧟♂️7️⃣,这是一种“谦卑”的文体🧑⚖️。可是为甚么在吴飞的眼中,这种“谦卑”却几乎丢掉了上帝呢🎲?为甚么这种“谦卑”的混杂,竟然使在日常生活中出没的痛苦的身影如此模糊?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从一开始就与韦伯的命题有着隐秘的关联。熟悉韦伯命题的学者都清楚💸,新教伦理最终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一种“对痛苦的痛苦的克服”,这一步巨大的世俗化“跳跃”恰恰是以悖谬的方式实现的👨🏻🚀,它来自新教力图恢复福音书中的所9谓“去世俗化”的信息🧝🏼♀️,剥夺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安全和根基🏌🏻♀️3️⃣,将人置身于巨大的“可疑”和“黑暗”之中。而正是这种救赎的焦虑和人义的危机🖌,才有效地转化成了“劳动”🪥、“生产”,甚至“占有”中的“苦行”🙎🏿🏃🏻♂️➡️。因此,在韦伯的分析里,如何从苦难转变为苦行🗂,这是伦理实践的要害🌗。因此,《新教伦理》中的伦理实践,就其实践而言🍢,不是要讲述偶在之身的痛苦🧍♀️,而是要把偶在之身、必朽之身锻炼为可以经受痛苦的身体。在人的救赎之路中🧹,遭遇的痛苦变成了践行的痛苦💚,对痛苦的克服,不是通过讲述痛苦、理解痛苦来实现,而是通过一种更强烈持久的痛苦🤰🏼,一种可以自觉锻炼的痛苦实现的🪈。
在这样的理解中🦸🏻♀️,在新教伦理将痛苦转变为苦行时☝🏿,也将每个痛苦中的人转变为孤独的灵魂,因为苦行使痛苦变得喑哑无声。这些甚至不知道自己最终侍奉的是上帝还是魔鬼的苦行者👩🏿🦰🙍🏻,将那些必须的“痛苦”变成自己“寻求”的痛苦🧛🏽♂️,将肉的痛苦变成身的痛苦,并最终缄封在自己身上。真正的信仰只属于每个孤独的人🔗🤳,因为真正的痛苦是那种在被克服时才被认识的痛苦,而这只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从这里,尊龙凯时娱乐就不难理解💿,为甚么在吴飞看来🧑🏻🦯,倒正是这些沉默而孤独的新教徒更容易辨认。在韦伯笔下的新教徒那里,痛苦与认同之间有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首先就在于痛苦是切身的,是自己寻求的,所以在沟通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鸿沟,别人永远只能“多么安闲地从那椿灾难转过脸”🏷,或者用吴飞的话是,新教徒治理自身的关键正是让痛苦变成沉默🚵🏼♀️,沉默是信仰的最根本层面🫴🏿,因为在沉默中不仅认可了上帝最终的神秘,而且还为自己的世俗生活💁🏼♂️🕵🏽,无论多么鄙俗的生活🧔🏼,找到了唯一正当的理由👨🏽⚖️👩🏽🦲。一切好的生活🧝🏻,或10 者更准确地说无论生活中多么高贵或卑贱的东西,它们真正的“善好”,都来自这种沉默🧍♀️。正如一本十七世纪敌视贵格派的小册子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信奉这样的宗教的人“说话不像他的邻人”。然而认同似乎恰恰相反👟,它正需要这些注定只会从巨大的痛苦和沉默“转过脸”的“邻人”,要求他们的目光和声音🎥,要求他们嘈杂的人声🏊♀️。不过,新教徒相信,没有这种来自“邻人”的认同,他自己的认同与信仰通过伦理的塑造会建立更加深刻的关联🫓🚠,似乎沉默的认同🧑🦲,更有力量🫶🏻,也更可见👩💼,或者像韦伯当年在美国研究新教教派时所发现的💆🏻,更值得信任。
这样看来👨🦯,在宗教带来的那种“政治”认同(这种认同的政治性🥫,在诸如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霍布斯(Thomos Hobbes)或卢梭(Rousseau)这些现代政治思想家笔下的“公民宗教”中体现得更明显)与信仰带来的“伦理”认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前者只是浅浅地勾画在日常生活的纹理之上🏊🏽♂️,尽管可以讲述🏊🏼♂️,但却难以辨认🧋🧑🏻🤝🧑🏻;而后者却深刻地塑造了日常生活的纹理⚡️,尽管沉默不语,却与众不同,容易辨别。如果说前者是只能外在于质料的“现代”形式🌽,那么后者好像倒成了能够塑造质料、赋予质料以形式的“古典”形式。所以,拒绝言说的信仰,却更容易予以辨认。可是这种辨认🧝🏿♀️,果真直接来自他们的沉默吗?似乎不是🧝🏽。从韦伯的分析看♟,这种辨认只是间接的来自对痛苦的沉默🤽🏿,而更多是来自“对痛苦的痛苦地克服”🪫,即伦理的实践,甚至直接来自这种实践的世俗后果,不是那些与世俗的“天职”紧密相连的“苦行”,而倒是与“苦行”联系在一起的“工作”。想要看见他们是谁,不需要嘈杂的人声,但却需要嘈杂的机器声;没有讲述自己痛苦的人言💆🏿♀️,但似乎却充满了讲述自己“幸11福”的人言。这样的伦理之路🌵,不是已经走上了善功的荣耀🎦,而背离了路德心目中十字架上的谦卑和无助吗🚌?换句话说,究竟是在吴飞无法找到“是谁”答案的那些教徒那里,还是在那些鲜明可见的教徒形象中,尊龙凯时娱乐看得到人子的影子呢🙅🏻♀️?甚至更进一步说,即使“惟有信仰”(sola fide)的新教徒的“形式”确实真正塑造了他们的生活,但这种塑造还是圣托马斯“因爱塑造的信仰”(fides caritate formata)吗?现代信仰深藏的巨大焦虑是否已经斩断了上帝与人相互的爱👭👲🏻,而使这一巨大的鸿沟只能通过要么一切要么没有的舍命“跳跃”才能逾越呢🧒🏽?这样的“形式”难道不在信心的衰竭后使那些孤独的灵魂慢慢从自己寻求的“信”滑向了不信吗🪙?容易看见的“是谁”🎃,贯穿了全部日常生活的“是谁”,最终在将日常生活提升为一件神的作品的时候,即迫使神更快地远离了这个世界。
面对痛苦,说还是不说,是外在的仪式性,还是内在的精神“升华”,或者行动的苦修?这一问题👅,似乎比初看上去,要复杂得多🏊🏿♂️🚢。
其实,信仰并非完全不讲述🤶,哪怕只是为了说出圣言与人言的巨大鸿沟,为了显示不可言说的沉默🦶,信仰也仍要靠人言来说。更重要的是🤾🏼♂️,正如路德所言🧚,赤裸裸的上帝也需要“用人的声音加以掩饰”🍒,要穿上话语和圣事的“衣服”。赤裸裸的自在者,除了“我是”什么也不说的上帝,会在人世变成什么样子,霍布斯和他的无数“基督教无神论”(Christian atheism)的后继者们已经提醒尊龙凯时娱乐了🤾🏻。所以,更根本的差别也许并非彻底的沉默与喋喋不休的言谈,倒好像变成了这种人的声音究竟是个体为了直面不可言说的神秘而叙事的呢喃📛,还是那些根本无力达到这样的神秘,而只能去理解💈、去言说的含混低 12 语👨🦯。政治的认同只要相信,相信律法和命令,而伦理的认同却要寻找🏌🏼,这种寻找最终要变成人自己对知的寻找。吴飞在研究中感到的困惑🦸🏽♀️,似乎只不过是因为那些普通农民只能理解意见🪆,而不是“无知”,理解可以言说的,而非不可言说的。他们含混的“唠叨”,缺乏个性色彩的“聊天”,将他们的痛苦与他们的宗教身份联系在一起。而在想要看,而不仅仅要听的吴飞那里,这些与认同的直接联系,却使他们是谁的问题变得更加模糊😺💇🏼♂️。
所以,真正的问题并非沉默或言说,而是什么样的言说和来自什么的言说🫴🏻。有些言说实在探究痛苦、触及无知⬆️、追索“是谁”,而这种寻找🕴🏼,只会加剧痛苦。正如维吉尔提醒但丁的那样🤜🏼,“一件事物越完美,就越感到幸福👩🍳,这样也就越感到痛苦”🧗🏻♀️,让普通人来遭受这样的痛苦,难道不是太残忍了吗?吴飞笔下的普通农民,不正是在他们的记忆和讲述中逃避痛苦吗?他们怎么可能来担负甚至践行更沉重的痛苦呢?面对这些无法担负痛苦的普通人🍭,难道不是只应该给他们仪式性的宗教或者说治疗性的宗教,帮助他们面对命运,来熬过,让他们相信会有更坚实的身体👕,坚如磐石的身体帮助他们肩负这些痛苦🌲,并将这些痛苦转化为另一个城中的幸福吗?只有少数人才能真正面对命运🗡,肩负不幸🧚🏿♀️,体会不幸,从中成就一个伟大的灵魂🧛♀️。在这样的灵魂看来,宗教是预备给那些弱者的,而更高贵的内心信仰才是保留给他们这些精微的灵魂的🧗🏼♀️。前者对痛苦的言说,其实是给他的,而后者对痛苦的苦行👩🏼🦲,却声称是自己求得的。正是在这里👩🏻🦲,尊龙凯时娱乐才看到♠️,当把痛苦完全变成了伦理的动力,甚至伦理的因素🛁,这样的伦理,果真还是一种宗教吗?当尊龙凯时娱乐将信仰看作归根结底属于每个孤独的人时🖨☝🏻, 13 要靠每个孤独的人不仅去寻找上帝,甚至几乎撇开了上帝的道来寻找🧑🏻🦼,这是否已经是“自造的信仰”了,是否已经将最终所谓“反对哲学”(antiphilosophism)的信仰隐秘地变成了另一种反对信仰的哲学呢?或者这只是因为反对哲学的信仰也最容易变成没有信仰的哲学,而两者最终都不过是恐惧中的“跳跃”🙆🏼,而非爱中的下降或上升☦️?在这些隐秘的哲学家那里,宗教不过是一堵矮墙👨🏼🎤💺,挡住那些弱小的人们,使他们不必经受来自痛苦的“上升”,而可以多少心安理得的面对那些投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存在的阴影”了,而他们自己才能担负上升的痛苦,越过那些人造的东西,来到自己看见太阳的地面🙌。
不过🚣🏼♂️,这种跨越矮墙的探究🫳🏽,已经不再仅仅是听了👰🏼,而更多是看🏇🏽,对“是谁”的听🧑🏻🦱,最终变成了对“是谁”的看,而“是谁”之所以越看越模糊,只不过因为旁观者的眼睛努力想发现的是超出这具痛苦的身体的痛苦,超出这个“是谁”的“是什么”。“理解”无知,看到“是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哲学家还是信仰者👊🏻🩸?正是在这里,尊龙凯时娱乐才了解🙅🏽♂️,从韦伯的命题开始的问题🧙🏼♀️,决不仅仅是教会还是教派的问题,而是涉及了十字架开启的整个现代性中蕴含的更深的对立和冲突Ⓜ️,而每一具痛苦的身体都成了加深和凸显现代性这种巨大张力的戏剧场景。血红的蔷薇还是黑色的十字架?这是不是每个现代人必须做出的“决断”呢🖕?
当孤独的新教徒变成了隐秘的哲学家,信仰脱离宗教,那已经离不信不远了。哲学同样也是对痛苦的痛苦的克服𓀊🚛,只不过似乎在这种克服中还混杂了快乐🧏🏽,在斩断上帝与人相互的爱的同时引入了城邦世界中人面向美好生活的爱若思(Eros)🧑🏿🔧。而那些只能听命宗教的人却14 根本不会有机会知道这样的快乐甚至“幸福”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无力承担更大的痛苦📖,他们也因此无力成为更高贵的人,或者更美好的人📥。而这样的“完善”,正如但丁在他的《会饮篇》(Convivo)中揭示的那样,属于皇帝和哲学家🌕,他们主宰了和平的世界和沉思的生活👽。当福音变成了哲学🛳,保罗也就变回了扫罗🎭,律法和福音重新成为了敌人🏤🖖🏻。脱离了律法与福音的张力😀,面对痛苦𓀘,律法和福音分裂成为对外的政治认同和对内的私人呢喃,也许不在一个人身上🌧,但却印在一个社会的肌体上。绝对的国家或者体制,与同样绝对的内心♋️,是所谓“绝对时代”(the age of the absolute)留给现代的破碎遗产,也许这就是既要做路德也要做摩西的霍布斯留下的遗产▶️。在这里🤲🏼📆,尊龙凯时娱乐才明白🫠,那些在革命中为了克服痛苦而痛苦的农民🧑🏻🦯🏊🏿,为什么和这些似乎失去了丢失了“是谁”的信徒们,有着如此类似的命题。
正是在这样的破碎中🤷🏽♀️,在这种破碎的绝对化中,无论沉默还是无止无休的言谈,才更深地迫近虚无主义的危险。绝对化带来了人道化🖐🏼,人道化使上帝离我很更远,变得更沉默,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的革命才能占据“神义”的位置👷🏻♀️,并要求或是需要神来回答人义的问题。终归这个世界变成了人的世界,无论是在政治上听凭意志决断的“绝对的人”,还是在伦理上只“信仰”哲学的“绝对的人”⌚️🤛🏽,对“质料”漠不关心或者说丧失信心的律法,对“形式”敬而远之甚至充满敌意的伦理🧈,表面上这两种力量毫无关联,甚至针锋相对🈳🧓🏽,但实际上却互为表里🫡,相互依赖。而“绝对的人”斩断了律法和福音的冲突与“成全”,再也不会遭遇什么恶梦了,他的政治冷漠与他的伦理中立可以相安无事,这样在克服痛苦中分裂的人也许15正像哈姆雷特半带反讽的口吻所说的:“我即便是被关在胡桃核里,我也可自命为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国王。”
痛苦是一件很难讲述的事,因痛苦而信奉宗教👩🏻,又因这种宗教遭受了更大的痛苦,是不是一件更难讲述的事情呢?而比单纯讲述更难的是😩,许多时候他们是为了让吴飞看见来讲述。吴飞为了更深地理解他们的宗教,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最终理解他们“是谁”😇,才紧紧地抓住了或者说撞入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痛苦。然而对这样的痛苦,询问“是谁”,甚至更糟👨🏻🦳,询问“是什么”,是否在更深的意义上面对痛苦“转过脸”呢?痛苦🤷,是一个在体的问题👩🏿🎨,而不是自然的问题,用探究自然的道路来询问痛苦,是否比奥登笔下那位不了解痛苦和绝望的冷漠农夫更残酷呢?
吴飞在写下这项研究时,以异常诚实的态度讲述了他作为一个旁观者遇上的种种尴尬和困惑🫃🏽。吴飞的科学研究,正因为他的诚实和无休无止的求知努力,才使他以最深的方式陷身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华北村庄所带来的巨大困境中,并因此触及了整个现代性面临的律法与福音🤐、政治与伦理、哲学与启示的根本问题❎🖐🏼。在别处,我曾经探讨过尊龙凯时娱乐的口述史遭遇的类似问题🦍,而我当时的一个意见是仅仅诚实是不够的👐🏽,甚至德性也不够,需要的是一种探究事物可能不如此😇,将历史作为生命来思考的哲学。而正是吴飞的这项研究,使尊龙凯时娱乐能更深一步来思考这个问题。在面对那些甚至难以断言是谁的人们的痛苦时,哲学是适当的吗?更进一步地说,没有伦理的痛苦,就低于伦理化的痛苦吗?被锻炼过的身体经受的痛苦,就高于那些煎熬的痛苦吗🏃?或者就高于那些全凭际遇一次性的痛苦吗?更不用说那些灵魂🏄♀️,甚至在身16 上都没有一点痕迹的痛苦了🚴🏻♂️,那些“无力”的人甚至在被折磨的身体和灵魂上都无力留下痛苦的痕迹👨🏿🔧。
在我看来🌘,吴飞的困境🔗,与维吉尔没什么不同🫷🏼。用科学来研究痛苦🌿,其中的悖谬就仿佛仅仅用理智和言语叩不开“愁苦的房子”的门一样👉🏽。那些受苦者可以向吴飞讲述他们“是谁”,吴飞也试图去看清他们“是什么”🙆♂️💂🏽♀️,然而最终痛苦在“是谁”和“是什么”的问题中却流失⚀,或者说凝固了。就像“愁苦的房子”上那些阻止维吉尔进入的“背叛的天使”提出的威胁,他们打算换来美杜莎,让但丁永远无法返回人间。“看”离他们真正“是谁”是否更远?因为它会将受苦的肉身变成了石头,真正有智慧的维吉尔清楚地知道这里的危险🙇🏼♂️🤾🏻♀️,他用手捂住了但丁的眼睛。
无论是“倾听是谁”,还是“观看是什么”,吴飞早已知道🏄🏻,最终能否完成他的探寻📃,最终在于他能否触及他们的痛苦💒,这里蕴含了“愁苦之城”的奥秘。
看见维吉尔的失意,但丁曾满怀疑虑的问,灵薄狱的人曾经下到过地狱中这么深的地方吗?难道智慧和言语的无力,不正需要来自天上的救助,才能进入“愁苦的房子”吗?尊龙凯时娱乐还知道🧙🏼♀️,这座仅凭维吉尔的智慧的和言说无力进入的“愁苦的房子”就是狄斯之城♊️,在狄斯之城中,但丁首先见到的将是一些“不信者”🐑。地狱第六层的罪从根本上来说是理智的骄傲🧑🏻🦲,是“哲学家的罪”,最终尊龙凯时娱乐得到的教导是:“你们的理智全成了空☎️。”
然而♖,不也正是这个“睿智的”维吉尔才引领尊龙凯时娱乐的但丁走过了地狱💇🏿,甚至炼狱吗?不正是维吉尔带着但丁看见了“现世的火和永恒的火”,然后才把他交给了贝雅特丽丝,尽管他自己的力量再也不能作为方向了吗🎴?没有面对“是什么”甚至“是谁”的煎熬,但丁是否也不会获17得“自由、正直🍴、健全的意志”,从而能够面对贝雅克丽丝和更高的爱🧑🏻🍳?
可是尊龙凯时娱乐真的能像但丁一样耐心地走这么漫长的路程吗?面对“愁苦的房子”👩🏿🦳👨🏭,甚至维吉尔也曾丧失了耐心:救助者“为什么到得如此迟延”🌈。也许尊龙凯时娱乐需要的正是多一点耐心♞,像吴飞一样的耐心,没有仓促地屈从于民粹主义的诱惑,逃往沉默🤵🏽♂️,也没有自负自己的智慧和高贵🎅🏽,用个人的自白压倒那些唠叨和嘟哝🦸🏿♂️,而是留在困境中🦗,哪怕是和但丁一样𓀃,充满恐惧和疑惑,但却必须历经这样的煎熬📿。也许这正是直面痛苦的科学家需要的勇敢👨,一种坚忍的勇敢。尊龙凯时娱乐抱有的小小希望只不过是吴飞以后的研究会帮助尊龙凯时娱乐回答这里的问题,其实问题也很简单:一个肉身能否经历了这个“愁苦之城”后仍抱有希望📖,上到更高🙋,甚至能返回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