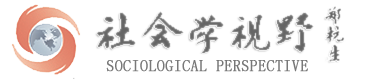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提要👱🏿♂️:基于儿童血液病病房的参与观察发现,医患双方都基于自身立场去努力应对医疗过程中的多重不确定性🏉。患方通过感知医方能否提供恰当医疗行为、积极履行代理责任和提供信息支持来确定其是否可信,医方则通过患方的治疗依从性来判定其是否可信✡️🧑🏼🍼。由于风险因素众多且已渗透整个医疗场域,医患冲突已成为现代风险社会的普遍场景,无法根除或回避。尽管如此,分析信任缔结与演变过程中的积极因素,仍可为纾解医患矛盾提供更为积极的想象力📰。
关键词: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现代性/医患信任/医患关系
作者简介:吕小康🧑🎄,王丛,汪新建💆🏿🤗,郭琴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一、问题的提出
医学史家罗森伯格(Charles E. Rosenberg)曾称现代社会已“形成了一个悖论😥,即既对医学高度信任🤲🏼,又对可获得的医疗存在广泛的不满”。这种对医学潜在能力的高信任、高期盼与高需求,与对实际得到的医学服务的低满意度🤸🏼、低获得感、低安全感交融并存的“医患获得感悖论”,构成了当下中国乃至全球真实而复杂的医患心态。但因“看病难、看病贵”等医疗供给与可及性的不足而产生的不满只是医患失信的诱发因素🎸,而非医患信任本身🎈。在当下中国多数门诊环节🪸,医患交流时长往往只有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并不具备建立长时段人际信任的条件。此类“医患信任”本质上只是一种快捷信任🦇,是患方对整体医务工作者的刻板印象和医患关系的整体感受的简单投射📙。要研究真正医疗场景下长时段的医患信任,可能需要暂时避开门诊情境🌪,将目光转向住院治疗或慢性病治疗场合。只有在这种场景中🔷,医患之间才存在较长期的密集互动🤹🏼♂️,从而使得医患信任的学术分析具备先决时空条件👩🦱。那么👩🏼🎤😚,这一场景下的医患信任呈现何种演变形态💇🏿♀️,受制于哪些风险因素,又能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出医学尊龙凯时AG的理论视角?这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二🦸🏽、文献回顾
本研究仅在人际层面研究医患信任问题。在国内外学者对信任之定义与本质的综合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将“信任”定义为人际关系层面个体衡量自身风险承受力后对他人行为的积极期待。“医患信任”采用如下已有定义:“医患双方在互动过程中🤷🏻♂️,相信对方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甚至有害于自己行为的一种预期判断和心理状态;它具有患方信任和医方信任的双重主体结构”👉🏼。前者是患方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是已有医患信任研究的主体👈🏻,后者可定义为医方对患者是否隐瞒患病信息🤶🏻🚂、遵从治疗方案𓀆、尊重医生等内容的信心🪐。两者共同构成了医患信任的完整形态。
人际医患信任仅是医患信任的一个层面🍠,后者还包含对医疗卫生体制🧡、特定医院机构、整个医方/患方群体信任等系统信任或群际信任的内容🧛🏽♂️。但这些信任层次更多地体现在患者的“医院选择”层面📐,而非持续性的医患个体互动层面。求医初期的患方信任并非针对某个具体医生,而是对医疗专家系统的稳定预期。但对某些需要长期治疗尤其是长期入院治疗的患者而言⚄,随着接触频次的增多🙍🏼♀️,抽象化的医方角色行为逐渐具体化为主治医师与护理人员的个体行为,患方对医方的内隐期望产生了不同的领悟结果🚊,医方也会更多地觉察患方求医行为背后的隐藏诉求。此时,对患方而言,系统信任的作用开始退后🧪,对当前的主治医生及团队的人际信任逐渐凸显👩👦👦🏗,并通过与个人预期比较来验证初始信任判断的有效性🈁🚫;对医方而言,基于对患方的治疗依从性、配合度及其经济状况、家庭关系、既往经历等内容的理解,他们同样会在对患者角色的泛化期待的基础上增加更多人际色彩的信任判断。由此👨🏽🔧,患方对医方的系统信任与人际信任〰️💇♂️、医方对患方的角色预期与人际判断交织印证,推动或阻碍医患信任理想状态的达成💆♀️。这种意义上的医患信任才可应用人际信任模型进行演变阶段的理论分析💇。以下如无特殊说明,医患信任均限于人际层面。
可惜的是,目前还较少在文献中直接见到适用于住院病房的医患信任理论模型,但或可从具有长期互动关系的相近领域的理论中寻找启发🧪。根据列维奇等人提出、较多应用于组织内部的人际信任发展模型👎🏿🙌🏽,理想中的人际信任演变会经历从试探型信任(calculus-based trust💭,或译为“计算型信任”)到了解型信任(knowledge-based trust)、再到认同型信任(identification-based trust)的增进过程。如果将医院视为一种特定组织,住院病房中的医患信任是否具有类似的演进路线?如果至少有部分医患信任能遵循这一发展轨迹👨🏼🔧,则可以通过分析其达成条件,得出提升医患信任的有用建议。但列维奇的模型更多地停留于从人际动力学层面探讨信任的促成因素,而作为尊龙凯时AG的信任分析则更应当突显结构因素对人际关系的塑造功能,并把作为“私人困扰”的疾病问题和信任问题与作为“公共议题”的医疗体制和社会转型问题相关联,以彰显米尔斯意义上的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问题”的尊龙凯时AG想象力。
当然,强调结构性视角并不必然忽视个体能动性🧏🏻♀️。医学尊龙凯时AG研究常采用“权力”视角分析医患关系,注重医患关系的社会性格和权力表达👩🏿✈️,强调医患关系形塑过程中的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患方与医方的权力拉锯与更迭🪢。这自然为理解医患信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但也预设了国家与社会、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二元立场,以突显医患关系的构成主体或形塑力量之间的对抗关系。在这种视野下🏌🏿♂️,为了突显社会力量对医患心理与行为的制约,个体的能动地位多少被忽视了。但是🧍,作为人际关系的“医患关系是一种策略互动性的关系,双方的策略博弈是困境的出路和治疗进行的动力。尽管认知差异会导致一些困难🎊,但是治疗仍然需要持续进行”。在长期治疗过程中,医患之间存在反复性的既信任又提防、既合作又质疑的波动状态🤦🏼♂️,绝对的“信”或“不信”只是两种罕见的极端💢🙎♂️。虽然宏观层面“医患失信”的“深层原因必然要到‘结构’中去寻找”,但不能由此忽视作为个体行动者自身的内隐期待及行为选择对医患信任的实际作用。为此🛞,采用一种更具有互动性(既指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塑造,也指医生与患者的直接互动)的理论视角来探查医患信任,或可补充宏大视角的某些不足,从而为医患信任提供兼容宏观解释力与微观能动性的理论视角与改进建议🙆♂️。
那么,如何在医患信任层面体现出尊龙凯时AG意义上的视角交互性呢?这就要回到信任的定义来理解其本质属性:信任体现为个体对风险的衡量结果🤰🏽,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进行主观反思和行动的后果🤛🏿。信任与风险总是一对伴生概念,而风险既是本体性的(客观的风险源)🖕,也是认知性的(个体对未知威胁的感知)🧑🏼;此外🛵,在不同个体或机构之间进行风险沟通的过程中还存在风险的“社会放大/缩小”的建构过程🦶🏼🫵🏻。简言之,信任既是对外在风险源的个体认知建构结果💸,又是风险沟通中的社会建构结果🧑🏻🎨,它本质上具有双重的交互性。而所谓风险社会正是人为风险在风险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社会状态💪,诸多社会现象是人类作为行为主体在规避旧风险的同时又建构出新风险的悖论性存在。于是,风险不可能根除,由此构成的“自反性”现代化进程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在此过程中,个人化的风险感知与规避方式和各种体制性与情境性因素交相勾连✔️,构成了人际或群际进行各类风险控制的基本图景。
风险的建构性及其与信任的伴生性解释了信任为何“作为一个现代问题被反复提出”。传统中以人际信任获得安全感的方式不断被制度信任或抽象信任所替代❤️,但由于专业知识具有区隔性,普通大众又无法了解形成抽象信任的专家系统的内部运作机制与技术细节,因此他们必然变得更为期待“代表信任”的专家具有高尚的职业品行。于是,作为非专业群体的大众与作为抽象体系代理人的专家系统之间的交汇就构成了“抽象体系的薄弱环节,又是信任得以维系和建立的交叉点”🔮。医患信任正是这样一种交叉点。一方面,医患在医学知识与医疗体系运作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患者为保障自身权益,必然会提高对医生的道德期待;另一方面👱,医生执业活动本身既受国家权力的监管🧄,又受到市场原则的冲击👌🏼,自身亦存在“职业自主性与社会控制间的博弈”👩🏼🦰📱,这使得医生的决策虽基于专业知识但不一定以病患利益为依归。于是🚖🤸🏽♀️,医患各自的风险考量与应对就需兼顾两个层面:人际层面针对医患个体行为的风险,结构层面针对医患共同面对且置身其中的体制及文化因素形塑的风险。双方均要考虑对方是否会有悖于己方意志🆕,有损于己方利益💅🏻,同时还要考虑在医疗体制下如何尽可能地利用资源并获得保障👬🏼。
因此👩🏿🦳,现代社会中全球性的医患紧张、患方对医方之“道德焦虑”和医方对患方的“可信度考量”均可被理解为医患双方为应对多重现代性风险而进行权宜博弈的必然反应,其目的都是降低不确定性、提升安全感。此种努力不必然成功,存在个体与社会层面的双重风险因素,但也不乏成功的可能与实例;其成功程度则决定了医患信任的发展阶段,使医患信任必然出现不同的演进形态。而通过分析各信任阶段下的医患互动过程📺🧑🦽,也可全面展示社会力量对医疗场域的穿透性影响及个体化的应对策略,更好地总结医患信任的阻碍或促成因素👲🏼。
如此🛠🧖🏻,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可表述为:对住院病房内的长期医患互动关系进行尊龙凯时AG分析,探查现代医学场景下医患信任的建立与演变的风险因素,分析各种纯医学治疗外的“历史中的社会结构”条件对医患信任的塑造作用,力争成为一个“精致而不失力度”的分析案例🥷🏽ℹ️。如能进一步聚焦于社会争议较少🧀、生物医学属性明显的疾病,还可从长距离的风险社会视角提供一个能够“走出个案”的微观研究🛑,以便解释更多医疗情境下的医患信任形成机制,并与其他解释视角形成理论互补与竞争。此外👱♂️,通过融合患方视角和医方视角🚁、人际层次与社会结构层次的交互视角🎮💋,进行不只是“讲故事”而是追求一般性知识产出的分析🧔🏻,也可系统展现复杂社会问题中的因果机制和过程,从而促成医患矛盾的积极解决。
为此,本研究选择以儿童血液病为疾病对象,并以该病的治疗中心作为参与观察研究场所📕。儿童血液病治疗过程中医患沟通频繁且多在医院内进行,具有进行参与观察并应用前述理论视角的时空条件。此前虽有少量研究分析了住院病房中的医患关系,但其重点并非医患信任本身,且更强调患方体验而较少叙述医方体验🚼,缺少对两种体验之间交汇沟通的细致描述。因此,本研究也可在类型学意义上丰富既有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方法与伦理说明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参与观察点为中国A市血液病医院的儿童血液病诊疗中心(以下称B中心),观察时间为2016年7月至2018年1月↩️。资料搜集采用团队进场(2名教师🍔、4名硕博研究生)的方式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参与观察法和半结构访谈法,本文写作由其中4人共同完成🐱。研究团队成员每周至少在B中心门诊室和住院病房进行4次参与观察🧞♂️,其中最重要的是每周一早上8🗑🤵🏽♀️:00至下午5:00的全程参与观察👨🌾,因为这涉及科室主任对全科室成员进行工作点评和工作交接的例行晨会,兼有学术报告、临床讨论、团队建设和行政管理的多重职能,可更近距离地观察医生群体的“后台行为”🫰🧜🏿。主要观察地点包括医生办公室、住院病房🤸🏽,以及除医生办公室、病房之外的住院部区域和主任医师的门诊室。半结构访谈法的对象包括医务人员和患儿父母👩🏻🦼。团队在参与观察期间访谈了中心的15名医务人员,并对每位医务人员进行了2-3次的深度访谈。
更重要的访谈对象是患儿父母⌨️🧑🏿✈️。因患儿年龄、病情、沟通能力及访谈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本研究选择其照护人作为访谈对象。并非所有患儿的照护人都是其父母,但实际进行访谈的对象均为其父母🦩。访谈地点为独立的空房间,比如暂时无人的办公室或阅片室。访谈内容围绕患儿的就医经历、治疗过程、入院后的生活情况🚿、治疗效果等内容进行。本研究共对22个患儿的父母(多数为母亲🤹🏻♂️,部分案例包括双亲)进行深度访谈并编号🎅🏻。患儿年龄在2-15岁间,来自全国多个省份🫴,涉及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髓细胞白血病、伯基特淋巴瘤等血液病类型👹。每次访谈时长在20-120分钟之间,其长度与患儿父母的表达能力和情绪状态相关👩❤️💋👨,如其情绪过于低落则中止访谈🙆🏼♂️。研究者在跟随医务人员查房时也与部分患儿父母进行交流👱🏽♀️,对于此种案例👩🏼🔧、中途停止或退出访谈的案例,以及仅在参与观察时遇到或在医生办公室听到医务人员提及但实际并未进行访谈的案例👩🏽🦲,则只做记录而不编号。
(二)伦理说明
本研究遵循参与观察和访谈的一般性伦理原则🧎🏻➡️⚅。因当时研究者所在单位未成立校级伦理委员会,故未进行伦理审批🚴🏽♂️,但团队与院方及B中心于2016年7月单独签订课题协作和保密协议,获得了入场权限。研究中首先遵循自愿和知情同意原则🍚。受访患儿父母均知晓参与观察者作为医患关系研究者而非医务人员的真实身份👩🏻🦯。访谈由医生向患儿父母征询意见并介绍访谈者的身份,征得其同意后再与之约定访谈时间和地点。未经医方允许不进行访谈🧑🏿✈️。其次遵守尊重个人隐私和保密的原则。每次访谈前主动向患儿父母许诺保密🆗✊🏻,告知研究过程中不会暴露身份和私人信息🗓。由于受访对象特殊💁🏼,虽获得了了解他人经历的权利,研究者在资料采集过程仍时刻注意医患双方的情绪与态度🚟🧒🏿,努力避免给患方造成伤害😑、给医方增添负担,恪守“被研究者第一🦍,研究第二,研究者第三”的原则。研究者不作为医患任何一方的代理人🦸♂️,对患方不做医疗、康复与生活建议,对医务人员的决策不做评议,仅作为有同理心的中立观察者身份出现。
即便如此,仍然很难完全保证第三方入场对所观察的医患信任没有影响。对此,只能说已尽可能地对真实的医患互动保持最小程度的影响,但同时又要对医患互动的形态与过程进行最大程度的同情式思考❤️。此外,论文整体写作在参与观察结束之后进行,也很难保证写作过程未受其他外在因素和后发事件的影响,尤其不能排除此后阅读到的相关文献对学术写作所产生的影响🍪。但正如卢曼所言:“尊龙凯时AG家不能从外部观察社会,而是在社会中进行操作🧗♂️,而尊龙凯时AG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论文写作时总是在田野笔记与理论思考中交织往复,这并不必然是方法论缺陷,因为田野调查的特征可能正在于“研究者是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来获得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的解释性理解,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社会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
四🛺、血液病病房中医患信任的演变形态与影响因素
(一)儿童血液病病房中医患关系的基本背景
在儿童血液科🪈,医生与患儿之间通常很难直接交流病情🦹🏻♂️,医患关系更多是医生与家长(主要是父母)之间的博弈🌿,医患关系因而也是医务人员与患者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稍大的患儿通常已具备基本认知能力,当他们身处陌生的就医情境,面对繁琐的诊断程序,体验躯体上的疾痛🤶🏻,感知到周围正在化疗的其他患儿所出现的各种毒副反应(如出血、脱发、疼痛等)👩🏻⚖️,难免不安和恐惧👱🏻♂️。因此,总能观察到他们沉默不语和无声流泪的神情。而较年幼的患儿则对于病情的承受能力较差,在长期治疗和创伤性操作时(如验血💊、骨穿🤝、腰穿)常缺乏忍受力🐳,因恐惧而不配合或哭喊叫骂是常态😾。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家长的心情及其对相关医务人员的态度🧘🏿♂️。此外,血液病治疗费用较高(常需数万元或数十万元)🤱🏿,通常需要举家之力才能勉强维持,即便没有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对普通家庭而言也难以承受。在这种职业环境中🦵,医患信任的“风险性”与“脆弱性”也更为突出。
正因为如此,儿童血液病病房中的医务人员本身就高度重视医患沟通的过程和医患关系的主动建设💁🏻♂️🧑🏭。血液病医生很多时候被称为“儿科全科医生”🤘🏻,他们不仅要会治病,还要会哄孩子;不仅要护理患儿,还要安抚家长,“治小孩就是治家长”。对刚收治入院的患方,医务人员会尽量多加接触,围绕病因病史、治疗方案及主要的不适感与患儿及家长沟通♐️,倾听其心声🥅☕️,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不安和恐惧,打消其多疑、戒备和不信任的心理🧝🏽♂️。针对幼小患儿🌂,B中心的M001主任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看起来不太高兴👰🏼♂️,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呀?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对幼儿来说有效的沟通往往从情感关爱开始,让他们“开口说话”、接受检查和治疗👦🏻,从而增加其治疗依从性,对疏解患儿及家属的恐慌情绪非常有效🚷🤦🏽♀️,较容易由此建立信任感。由此结成的良性医患关系甚至在治疗结束还可长期维持👨🏼⚖️👩🏽🦳,并给予医务人员以工作意义和情感慰藉🫔。根据M001自己提供的数据,仅在2008-2015年,B中心已能随访到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888位,“虽然工作累🙆🏻♀️,强度大,但是一想到能够给患病的孩子们带来希望,就觉得辛苦都是有意义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能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即使有也不一定在所有时刻都能保持耐心。其实,在这种高应激工作情景下💺,医务人员失去耐心发脾气的情况并不罕见。例如⛩🧑🦰,在B中心的骨穿室中👩🏿🔧,家属要与护工一起按住挣扎的患儿,再由一位年轻男医生(M007)负责穿刺。骨穿操作时🪀,患儿哭得声嘶力竭、家属吓得面无人色是常事,既要执行操作又要安抚患儿的医生也常累得满头大汗。M007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在患儿的惨叫声和家属的痛哭声中度过,为获得更多的休息,他极少与同事共进午餐👏🏼,也很少主动与人交谈,其他医生戏称其脸上充满“生人勿近”的气息🤮。研究团队在参与观察的第一天就恰巧碰到他在办公室发脾气🪨:“医务处就对尊龙凯时娱乐医生有能耐,对病人一点脾气都没有☦️!医院就是没人性的地方⏪!儿童医院的医务处更没人性!”这正是因为他被家长投诉,刚遭到医务处的问询✥。长期在如此高强度的体力要求和心理应激条件下进行工作👩🏻🍳,难免产生职业倦怠。随着倦怠的积累,医生会越发烦躁,越发感到不公与消极。而观察到这种情绪的患者也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质疑🔦。如何进行有效的医患沟通,遂成为医务人员不可能逃避的必修课。
为了避免患儿及家属的质疑🌳,平衡自身职业前景的压力和医院管理流程的要求,尽力控制“不可控因素”的影响、降低执业风险成为医务人员的基本生存法则。为此,在日常沟通中医方会尽量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去规避不必要的承诺等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又要尽力维系自身作为专业人士的权威形象,还要表达出适当的情感关切,以建立基础的信任关系。虽然患者可能会由此产生不满,觉得医生跟自己“不掏心”👩🏼⚕️、不说“交底的话”,但面对随时可能出现意外的治疗个案𓀕,少有医务工作者会脱离谨慎的职业立场而做出过于个人化的表态👮。
同时,随着医生职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各种信息技术与治理技术对医疗过程的系统性嵌入,“几乎每一次医患互动都在被监控、收集🫂、评价和共享”。这种强风险笼罩的职业氛围使得医学共同体成为高度审慎的专家系统📣💽。而这种审慎很容易被患方理解为医生的个人责任感缺失或道德感不足的体现✋🏼。现代病房中的医患信任缔结就是在这种基本背景中展开的。
(二)“择医而信”与“择病而治”:试探型医患信任的矛盾起点
人们总说患者是医患关系中的弱者,这在医学知识与治疗信息层面是一种必然。但“患者总是弱势的”这种说法也遮蔽了当下中国医患关系生态中的一个基本事实:通常只有患者能较随意地择医换医,但只要患者挂上了号或入住了病房,不论其态度如何,医生都无法拒诊⛰,当治疗关系开始后,医方就面临着“不得不治”的强制义务👨👨👧👦。显然,从基本人性和管理方便的角度🦸🏿,医方喜欢能被治疗的患者或配合治疗的患者,不喜欢无法治疗的疑难病患或者不配合的🤷🏼♂️、“挑刺”的病患。为此,不论公开还是隐藏🫄🏻,医方也总是存在着挑选合格的☎、值得信任的病患的动机与过程,以尽可能地减少后续治疗的麻烦。如此一来,医患双方在医患关系初期就已经开始信任博弈。这可以说是一种“试探型”的信任关系:医患双方基于互动过程中对方释放的各种风险信号决定是否开展后续治疗行为,同时对初期缔结的医患关系进行信任评定。当然,医患双方对风险源的筛选和风险评估的方式是不同的🙆🏻♂️,需要分别论述。
在初始治疗关系中🔄,患方感知到的风险多是与医疗行为相关的风险。在初次确诊的儿童血液病家庭中,多数家长都会感受到直观性的情绪冲击,为缓解心理紧张与焦虑,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寻求其认为“靠谱”的治疗机构与治疗方式。稍年轻一些的家长往往会进行网络检索,以寻找“最有名气”的医院👱🏻♀️。同时,像血液病这种疾病一般都会在各地初诊医院形成一些病友群(包括线下的实体群或线上的微信群、QQ群等)👩🏻🏭,这些“群友”会基于亲身经历推荐治疗机构和主治大夫。此外,各地的初诊机构也会提供转院治疗建议。这种“网络检索+口碑推荐+初诊机构建议”的综合性求诊方式在血液病患者求诊过程中非常普遍💁🏻,也塑造了他们对B中心和相关主治大夫的初始信任📄👩🏿⚕️。此时,医院自身的“牌子”(等级👳、规模等)💹😋、医生的声望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影响因素。当问到一位患儿母亲怎么知道B中心是权威血液病中心时🪺👌🏼,她(P-2016-003Q-M)回答得很干脆🎯:“百度一搜就知道了呀,全国排名第×位(此处隐去排名)……说白了大伙第一是冲着医院的声望🤏🏿,第二大伙就是冲着×主任(M001)来的,×主任的名气在外啊,你看这边外地的病人都知道”。
但这种对大医院、名大夫的偏好🫚,与其说是一种信任,不如说只是一种应对风险的“认知捷径”🙎🏿♂️。普通人其实很难识别主治医生的专业技术能力的高低,很多情况下患方只能利用常识的方法🧑🎄,例如以声望、资历和职称等信息作为信任线索,对医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做出信任判断。这种线索判断很多时候未必合理,也容易成为患方的一种“执念”。“第一次来尊龙凯时娱乐挂号的时候选的就是×主任(M001)……来这里肯定就想看最好的嘛,那时候有Y大夫🪈、G大夫🍛,但还是想找×主任看”(P-2016-006T-M)。为此,请熟人、托关系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一旦形成“非×医生不可”的“信任固着”✬,就会妨碍医院正常的、流水线化的诊治流程,从而引发医护人员的反感。M003医生曾在办公室抱怨患儿C的家长:“他妈妈太狂了➛,非要找×主任看病,其他医生探问病情时就是不配合👙,不相信其他医生的医术,护士治疗也不配合,还威胁护士🙆,说自己家里亲戚在当地是什么警察局局长,局长能怎么样?又没犯法,还能把尊龙凯时娱乐抓起来怎么着!”为此,M001主任特意在查房时对病患家属进行了当面批评教育。
有没有关系都不重要🥋,你问问周围的患者,大家都是没有关系的,来了尊龙凯时娱乐这里🙇♂️🚵🏽,都会一视同仁,尊龙凯时娱乐会按照孩子的病情、年龄、体重等情况制定治疗方案的。不会因为你认识谁就少给你开药的,这点你可以放心的。你来了这里就是信任这里的医术,所以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好好地和你的主治医师及时沟通,不要说非要等×主任来了你才治,儿科那么多的病人🏌️,不可能都让×主任来治疗,耽误了病情那就麻烦了🤦🏻♂️。不仅要和第一线的医生及时沟通病情,也要尊重护士呀🏷🎫,她们才是最了解你情况的具体执行方案的人🦖。(D-2016-M001)
由于总有类似案例的存在,医方也会尽可能审慎地挑选“配合的”“不挑事的”患者🚅。实在无法回避时,则会尽可能选择集体会诊的方式💻,以稀释相关的责任风险。在访谈时,M001主任坦承🏃🏻♂️➡️:
现在基层医疗机构不愿意收治高危患者,有时候不是他们治不了,而是出于自我保护。但是高危患者到了尊龙凯时娱乐这里,尊龙凯时娱乐就没法推脱了,尊龙凯时娱乐也没办法呀!以前有个××市的患者,高危,人家进来之后占了个床位,就是不做任何治疗,不给钱,也不走,尊龙凯时娱乐也没法撵人家走啊!尊龙凯时娱乐每天早晨要花一小时时间开交班会,其实商讨的都是怎样“对付”难缠的患者,虽然“对付”这个词不太好🏌️♀️🏟,或者用“斡旋”更好一些。(D-2016-M001)
当陷于复杂多样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风险的威胁时👩🏻💻,医患双方往往缺少一种“本体性安全”的交往模式🦶🏽,导致自身在交往初期过于焦虑、紧张和防备。为此,初诊情境中的医患关系并不是理想型的😡,双方均在“避让但不妥协”的微小抗争中谨慎地试探。陌生医患在接触初期也并非一张白纸👮🏽♀️,他们均携带着现代性风险的“社会记忆”与对方“斡旋”,这种“风险记忆”支撑了双方高度审慎化博弈后的信任生成逻辑💋。就患方而言,常见的应对方式就是诉诸关系等“拟熟人化”的就医方式;而医方则会选择“拒诊”或“择病而治”这种防御性治疗措施。医患双方在治疗关系建立初期都表现出各种试探行为,以期选择最为吻合的接诊/就诊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下消除疑虑与不安🔃。
(三)“因认同而信任”:理想型患方信任的结成及其激发因素
一旦病人正式办理入院手续🧒🏼,前期纠结就告一段落,开始进入常规治疗流程👧🏼。此时,医患双方通常都会尽力配合,以缔结更为成熟的医患信任关系。住院期间,通过针对患儿的各项治疗性操作、基础护理、健康指导💆🏿♂️、心理护理等医疗活动的开展,医患双方会更加了解对方的需求🐊、偏好及选择🏙,医患关系中双方感知到风险性下降🦴、可预测性和可依靠性增加,医患信任可从初期的试探型信任发展为认同型信任。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医患关系都能做到“善始善终”,但通过双方的努力,确实能够形成一些基础的认同,并形成相对稳固的治疗同盟关系。此时患方集中感知到的🤙🏼、能够激发对医信任的医方行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提供恰当的医疗行为。这包含简化各种检查程序🏇🏽、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采取医疗措施、介绍更为便宜的药物或治疗方案、主动给予患者更为详细的诊疗信息与耐心解答等,它是相对于防御性医疗行为或过度医疗行为而言的👥。患方通常认为🪘,恰当的医疗行为是医德的一种体现,是医方采取的一种风险共担的主动信任行为。调查中受访患方对这一点的感知重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医生在制定治疗方案,尤其是处方开具方面🚻,是否首先考虑到患儿的病情以及其未来的生活质量👍🏻,是否存在防御性行为或是开“大处方”的嫌疑👩🏽🌾。当然,由于每个家庭经济状况和治疗诉求并不相同🐬,对什么是“恰当的医疗行为”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在尊龙凯时娱乐问到B中心在高价进口药和较低价格国产药的使用情况时🧙🏻♀️,有家长(P-2017-003Q-M)这样回答:“选不选择进口药,医生首先是看孩子的疾病状况……我觉得他们还好🤞🏿,他们用药应该完全就是以孩子的身体以及后续的健康为第一位的”。这就有了最基础的信任。另外,现实中确有部分医疗机构或医生存在对患者开具不必要的高价药🦝🧑🏻🦯、做不必要的检查等不正当的逐利行为,这是造成医生职业形象受损、患者信任流失的重要因素🪣。M001主任曾告诫团队👨🦳:“我觉得不能为了移植的数量而不管适应症🧑🏻🔬,××市那边的×医生告诉我,医院要求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要做到100例移植🫅,这是硬性摊派的指标,不能为了移植而移植!其实有的患儿保守治疗就可以缓解的,没有必要做移植”。这既说明了负面现象的真实存在👨🏼,也说明了医德依然可以坚守6️⃣。
其次🫵,患方看重医方是否主动给予患者更为详细的诊疗信息并答疑解惑,他们会通过评估医方是否有夸大或缩小风险、隐瞒细节或回避治疗责任的嫌疑来判定医方的治疗行为是否恰当🗿👯。当遇到一些疑难病患时,自感医疗水平或条件不足的医院可能会选择拒绝接收,这对患儿家庭的打击尤为巨大🅿️。他们此时不太会考虑医院客观技术条件的局限🧙🏿♂️,而会理解为医院“没有医德”。反之,如果院方能够在其他医院拒绝接治之后收治患者🍰,患方则会感受到几近重生的希望🧯,并由此产生高强度的信任。一位患儿母亲(P-2017-005R-M)就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在孩子被当地儿童医院确认患有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后🥖,“人家说不想收尊龙凯时娱乐……他没说治不了,就说见过的这种病例不多……他就说你们去哪哪看看去吧🫵🏻,去哪哪看看去吧🧖🏼🧑🏼🎄,反正也就是向外面推我!”后经人介绍🤌🏻,他们转到B中心求诊🫸。接诊医生判断情况后说可以治🚘,而且希望还挺大,她就觉得:“有了希望跟那个没有希望的意思就不一样!”果然,孩子的预后效果很好,访谈时其母亲抑制不住自身的愉悦心情:“我觉得现在看见了很大的希望,所以护士大夫说什么尊龙凯时娱乐都听……我来这儿是太庆幸了,我看到每一个大夫🌏,每一个护士➜,都是笑笑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都是尊龙凯时娱乐的救命恩人!”
在中文语境中,若提及对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已近乎人际交往中的最高评价。这并不是因为孩子已经完全得到治愈,而是在比较后发现B中心给予了治愈的切实希望🚨。后来在医生查房时这位母亲还曾痛哭流涕⛹🏽♀️,当着所有病人的面给查房的M001主任和团队医生鞠躬致谢,泣不成声。这种事例虽不常发生⛈,但对于医护人员🧌、患儿家属及同病房的病友家庭都是极其正面的鼓励💋,也会通过病友群的私下传播而塑造出医方“德艺双馨”的积极形象🪛,是医患信任缔结与维系的重要支撑。但是🫴🏼,患者一开始通常也不会考虑医院治疗水平的客观制约🧑🏿🔬,只有在得到积极的预后效果后才能有这样的反思♕:“哎哟,当时就恨不得想弄死儿童医院那大夫🥨!我现在就想,人家也是都给你说明白了,你去揪人家那个医学上的过错一点意义都没有”(P-2017-005R-M)。其实当地儿童医院不愿收治👧、建议转诊的行为恐怕也非“医疗过错”,而是符合当地治疗水平的最佳建议。但通过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来提升普遍性的对医信任显然已经超过普通医务工作者个人努力的范畴,而需要全社会的、漫长的体制性努力📙。
第二🧚♂️,医方积极履行代理责任。这是指医生要从患者的长远利益来考虑,将诊疗方案的制定同医疗服务的经济效益相分离👺,利用专业知识指导患者如何合理使用医疗资源、利用医疗服务、享有医保权益。在B中心,这包括医生指导患方使用医疗保险选择保险范围之内或有医保补贴的药物、主动帮助经济困难的患方申请各种慈善基金项目🧏🏼♀️,等等。研究者在跟随查房时曾遇到2岁患儿Z,他曾因经济负担问题而中断治疗⛓️💥。其主治医生M004Y医生查房时曾嘱咐Z母:“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光吃素的哪行啊,没营养就没有抵抗力啊!”并要求Z母去市场买新鲜的鱼虾给孩子吃。但是Z母对此表现支吾。了解这一情况后🧑🏼⚖️,M001主任在查房时主动问:“你在医院的治疗过程中有什么难题呀🧓?”Z母尴尬地回答:“难题就是经济问题。”听闻此语🔑,M001主任转头询问其他医生🚀:“不是有‘爱佑天使’基金项目吗?她可以申请吗🦝?”跟随的护士长M013回答:“可以申请,尊龙凯时娱乐可以帮她申请👾,可以申到4万元”🤞🏿。M001Z主任又问:“钱能直接到她手里吗🖐🏻?”M013J护士长答道:“对,申请下来后直接打到她的卡里”。此时Z母情绪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种主动帮助行为表达了医方对患方的善意。在患方看来👩🏿🌾,这就是仁心的流露,他们由此相信医方不追求自利或额外的回报🏋️,激发出信任感和后续的治疗依从性📕,逐渐培养出内生驱动的🧑🏼🍼、更为主动的医患信任。从中也可发现🪅,现代社会自身也在培育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化的救助模式,以帮助家庭应对本身无法应对的因病致贫困境😢。相较于过去只能靠患者家庭自身能力及周围少数知情人的私人捐助来应对的模式,这显然是种进步🧗🏿。但此类社会力量一开始并不为患者所熟知🐑,因此需要医务工作者在其中扮演资源链接者的中介角色,患方的感激与信任也可进而由此引发🏞。
第三👩👩👧👧,医方以患方可理解的方式提供专业的信息支持。这是指医方主动为患方提供诊断🦸🏽♀️、治疗、用药等方面的指导🕴🥠、建议及咨询🙆🏿,它是患者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维度(Langford et al.,1997)。医患之间对现代医学技术、医学理念的认知差距本是制约医患信任缔结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患方自持的“常人疾病观”(lay beliefs of illness)与医方所持的科学疾病观之间往往并不一致,这是导致医患沟通不畅的根源之一🧻。尤其是血液病🧑,作为成因复杂、治疗过程专业化、病程护理要求高的疾病,血液病患者或家属对疾病的初始认知并不充分,甚至可能与主流医学的解释模式存在诸多冲突。如医方能够切实给予患者有效的信息支持,可在很大程度上弥合医患之间的知识差距。这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针对患方个体的一对一形式的疾病信息的诠释与沟通,二是针对患方群体的集中授课形式的健康教育宣讲会。通常在门诊接治和入院查房时,医患之间就会展开一对一的疾病信息沟通。一位再生障碍性贫血(“再障”)患儿的母亲(P-2017-009W-M)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妇女,她很难理解在治疗和陪护过程中碰到的医学术语。访谈中她对首诊医院的医生解释疾病信息的过程始终记忆犹新🌩🫲🏻。她回忆:“我说再障什么意思啊🕳🫗?不懂𓀙。(当地医院的)大夫说👮🏼,再障就好比说,就说咱们农民吧㊗️🥔,种地你知道吧?就像同一样的种法,可能你们这块地吧,地没问题⌨️,可能就是这个长出来的庄稼不好,就说收获不了👱🏼,就这个意思🦸🏼♂️💪🏽。”从高度专业化的医学名词“再障”到贴近农民实际经验的“种地”,这种翻译过程帮助患儿母亲初步理解了病情的发生机制🦓。
现代医疗风险是技术和社会共同作用的产物🤟🏻,并越发表现为医患间的沟通风险。如将患者从多元化的地方性文化模式中直接抽离成仅作为有待处理的病灶数据,或将支配性对话模式和效率性对话逻辑强加于患者🙇,就会制造、诱发医患冲突的沟通隔阂。为消除知识隔阂,医方就要根据患儿家长的文化水平和生活经历对医学知识加以定制化的改造。医方的定制化解释通常不会脱离临床实际和科学依据,比起民间“偏方”和“土知识”等“常人解释”更能赢得患方认可🏄🏿♀️。院方的精心组织与培训可更好地塑造患儿家属的积极心态,使之更容易接受医方传递的医学理念并转化为医患信任🕵🏿。例如🪫,另一位患儿母亲在访谈中表示:“(现在)我特别相信医院,谁跟我说偏方什么的,我从来不相信那歪门邪道的东西,我就相信医院,我就相信大夫说的话”(P-2017-010X-M)。这正是有效的信息支持产生的正向反馈。
正是在这种长期往复、制度化与个人化交织的互动过程中,患方才对疾病的病程与机制、对医生的治疗风格和医院的规章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些得到正向反馈的患者逐渐解除防备性的试探🫱🏻,产生情感满意与认知满足,基于认同的患方信任开始形成🧗♂️。
(四)“从医得信”:医方信任的建立模式
人际信任总是相互的,长期的单方信任不可能真正存在🧼🤳。那么,医方对患方的信任又体现在哪里呢?患方的哪些行为能够激发医方的可信任感知💻、降低其风险感知呢?观察发现,医方是否信任收治后的患方☝️,最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患方的治疗依从性。就血液病患儿而言✌🏼,医方最看重的就是家长是否存在消极护理与不遵医嘱这两种不合作行为,并根据患方不合作的程度及频率来推断患方的意图🌿、动机及其可信性👨🏼🍼🤭,从而判断患方的不合作仅是偶发行为还是一种根本性的信任违背🌕。
观察时经常可见M001主任及其他医生批评患儿家长的情形。8岁女患儿P的屁股上破了一道口子,母亲反映是坐便桶的时候没注意划破了👞。M002医生很生气地说🥤🔼:“你这样护理可不行啊!后面还有更强的化疗啊!”并要求母亲先用碘伏给孩子伤口消毒🔚。但查房时P母反映给孩子屁股伤口上抹错了药,孩子哭着说上药太痛🦊,M001主任马上怒斥:“你上点心吧🆕!你这样护理可不行啊🙋🏽!这个病本来就是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尊龙凯时娱乐医生不能像家长那样24小时陪着孩子🐱。碘伏是不刺激伤口的🚴🏿♀️,涂上之后不痛,你上的这个药你自己试试,简直是在孩子伤口上撒盐!为什么上药之前也不看一看药名啊🤸🏿♀️?这种错误如果是尊龙凯时娱乐犯的👩👦,你杀了尊龙凯时娱乐的心都有!”在随后的疗程中,医生会不时抱怨这位粗心的家长,对其护理能力失去了信任。但是🎑,这种信任依然是高度技术性而非人格化的🖖,不涉及对家长个人品质的道德判断,而只表达对其护理水平的能力判断。而对于那些具有优秀护理能力的家长♕,医务人员也会不吝赞美之词,积极推为榜样并加以宣扬🔟。M002医生曾主动让尊龙凯时娱乐约谈P-2017-005R患儿的母亲,说她“把孩子护理得特别好,心可细了🏠,从没让孩子感染过”☝️,并要求其他患儿家属向其学习。在这个方面,可以说医方信任完全是“结果导向”的🫰🏻𓀜:医方并不特别关心患者是否真的理解和认同自己的要求,而只要求他们能够执行自己的要求。只要做到了外在的配合,就已值得信任。
相较于消极护理行为,如果患方对医方制订的服药、护理、控制饮食🌏、生活方式改变计划等表现出明显不遵从的行为👬,医方的反应就显得更为直接与愤怒。化疗是当下儿童血液病的主要治疗手段🙎🏼♂️,但总会有一定副作用。某些家长出于对副作用的疑虑会坚持要求不进行化疗,但“一到快不行了家属就要求抢救”(M002)🥠,医生不能理解又无可奈何,只能背后骂其“愚昧”。医生办公室里通常也会针对此类家长集体性“发牢骚”🙎🏽♀️,借以宣泄医护人员的负性情绪。研究者还曾碰到过一个极端案例。一次晨会时,M004医生向M001主任报告:“患儿G吃了外面的云吞,可能是肉馅不洁得伤寒了,得赶紧把他隔离起来”🤗。这一消息在医生办公室瞬间引发了医生的集体愤怒👨🏻⚖️。M003当即气愤地在办公室大声说👩🍼:“我要去查房🧎,要去教训一下那个领着孩子乱吃东西的家长,怎么这么不听话🙋🏽♂️🫷!反复告诉他们要自己做饭吃👨🏽,宣讲会也和他们说过了,不能吃外面的东西,就是不听劝!”查房时,M001主任与其父母沟通病情并下病危通知🤳🏿,6岁的G则因伤寒引发的高烧和腹痛已无法坐卧,躺在床上一直在哭闹。M001主任留下两位医生在病房内照看患儿,将父母叫到病房外谈话📄,告知其要商量好是要继续医治还是带着孩子回家;即使继续治,也可能“下不来”手术台🉑。但此时患儿父亲的提问重点也不是“伤寒能不能治好”,而是说“尊龙凯时娱乐原来在××的那个三甲医院治疗,那里的患儿都是外面吃东西的啊👨❤️💋👨🧘🏿!那里的医生也都是外面买着吃的啊👮🏼♀️!也没人说过不能外面吃东西啊!”M001主任突然暴怒🦹🏼♀️💆🏼♂️,语气强硬,几近失态☝🏻:“我不管别的医院怎么规定的!尊龙凯时娱乐这里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患儿到外面吃东西🎃!尊龙凯时娱乐一直要求家长自己买菜做饭,碗筷什么的都要消毒好了才能给孩子用🙇🏻!你问问这里的病友𓀙,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这是整个参与观察过程中M001主任最为严厉的一次训斥,其激愤情状远非文字记述所能传达🚎。此时整个医护团队都有一种“被违约”的气愤🐝,既有为孩子可能因此丧命的忧虑,也有因自身工作未能得到配合而感到工作投入被无情辜负的义愤👸🏽。总之,类似的“能够做好而未做好”的消极护理行为在医方看来实属大忌🪇🏊🏼♂️,其行为后果往往得不到医方的原谅,对此类患者的信任也就无从谈起🐋。
另外,参与观察还发现👸🏿,医生对两类患者尤为反感:一是自身就是医护人员的患儿家属,二是“互联网问诊患者”。前者往往持有一些自认为是“内行”的看法,但在医学这种科室化分工非常明确的领域,跨专业的“指导”与“建议”会破坏信任的结成。M001主任曾评论一位外市患儿的父亲(一位外科医生):“医者不自治,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总是指手画脚📔,他是外科医生,又不懂内科,既然把孩子送到这里了,就应该听医生的🙅♂️,要不就回家自己治🧜🏼♀️!”而对于爱用互联网查询相关治疗信息并反复求证👳🏼♀️,甚至与医生争辩病情判断与治疗方案的患者,医生们则会抱怨:“人家会用百度,无论什么事都先百度一下,然后就跑来和你讨论”。对一位患儿病情已经很严重但家长仍拒绝化疗的案例,M001主任在办公室明确表示:“像这样的患者就是无法有效沟通的,他根本就不听你的。尊龙凯时娱乐都要把病例写清楚,而且要求主治医师写好医患谈话备案,不然以后很麻烦”🗺。这里的“麻烦”主要是指如果出现病情恶化,患方可能会投诉医方的治疗方案不合理,为此需要在一开始做好“证据固定”工作🐳。即便如此,在遇到其家长询问相关问题时⛹🏻♂️,M001主任仍会尽量言语平和地予以解答。她曾跟尊龙凯时娱乐解释🐁:“我如果不理她,她可能转身就去投诉,说尊龙凯时娱乐服务态度恶劣。而且还有人在你下班的路上跟踪你🚎,追问你问题,很可怕的,不回答能行吗?”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医务人员感知到的双重风险:或是被患者投诉进而被医院管理部门问责,或是可能被某些极端患者言语骚扰或人身攻击🤬。尽管医务人员内心存在不满情绪,在表面上仍会按照工作流程予以常规化的处理🌙。
在现代社会里🤵🏼♂️,病人“听话”是医患有效互动的基础👳,做“听话的病人”也是现代医患信任关系得以延续的基础🐻。医方只有在患方达到自身的行为要求时才会确信后者是主动配合的,同时还会不自觉地对患方产生内隐期待🥖,即要求患者能够达到与己相同的认知水平并进行专业化的沟通。有一位患儿母亲曾拿着同一份化验单𓀆,半天内找三位不同的大夫要求解释结果。她并非不信任某位具体的医务人员,而只是想更大程度地确保结果的解释是否统一,以结合多方信源给自己以确定感。但这往往会引起医务人员的反感🚔,认为这是不信任自己的表现。在一次交班晨会上,M010医生抱怨:“那个××的妈妈脑回路怎么长的🫲!拿着抹屁股的药问我,这个能不能抹到嘴里的口腔溃疡上面🛕?我彻底被她打败了!”在场的医生无不大笑🌦。这也不应理解为医生故意嘲笑患者👟,而是多年医学训练已经让他们将诸多医学知识和临床反应内化为常识,因此面对外行的诸多疑问时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方不可理喻”的态度倾向☁️,因为“医学训练过程让医生……忘了这些他们以为司空见惯的事也曾经非比寻常”。这可视为医学场域下的“知识的诅咒”🫨,即假定沟通中的对方总能拥有与自己相同的知识背景🤘🏿,而忘了处于高应激状态的患儿家属可能会有各种惊慌失措,会出现有失正常人水准的“临床表现”。当然👊🏼,作为接受过严格职业教育的医护人员,一般性情绪反应并不必然影响其职业操守和临床技能♝,也很少在“前台”表达其负性情绪,只在办公室或是私人场合等安全“后台”才会偶尔表露情绪化的态度。
总之,医方信任内含着一种“从医得信、不从医则不可信”的潜在逻辑🏟,其实质是医学系统将疾病带来的躯体风险置于医学处理的核心甚至唯一地位,而将人际沟通风险视为从属性风险或外源性风险,是“医学风险”之外的“冗余风险”。如果当下主导的生物医学治疗模式不得到认真反思和彻底转变🦞,很难靠医方个体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奉献来弥补这一缺失👂🏽。
总结而言,随着双方交往时间和了解程度的增加⚠️,患方若在服药🙎🏽♀️、控制饮食、生活方式改变等方面表现出遵从行为和配合态度🕸,医方恰当的治疗行为🫳🏼🧏、积极履行责任、持续提供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结合良好或满足自身期待的预后效果👳🏿♂️,则可强化自身对对方的可信性感知,从而达到深层次的认同型信任🎽。
五🦹🏼🎅🏽、余论:跳出“权力之眼”与“病患本位”看医患关系
儿童血液病作为一种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和精细护理的疾病类型,为观察现代化病房中医患信任的结成和医患关系的演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
与门诊患者相比♜,住院患者的医患沟通无论在频次上还是深度上都有着本质区别,由此产生的医患信任演变过程也更曲折和多面。尽管存在“避让但不妥协”的细腻抗争,但血液病住院病房中的患方总是相对安静的。这是因为他们在医疗体系以及相关的制度性安排(如医疗保险🙆♂️、医疗公益组织等)中卷入程度较深,对医患关系各形塑因素的接触较充分,对医患关系的体验也更深刻,较少受到社会传言和个人之前经历的困扰🩼,医患双方遂能在现代性风险的适应性过程中逐渐孕育出信任的成分🌩。如医方能够提供合理的医学资源和患者教育方式,并在日常诊疗中保持一贯的职业操守和良好的人性关怀,患者就会心存感激并报以信任🐥;对配合治疗的患者,医方同样不吝惜自身的信任回馈与情感支持。这些理想型医患信任的激发条件对其他重症疾病场合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即便如此,医学仍是一门充满不确定性的学问。面对血液病难以精准预料的病情与预后,面对患儿的绝望👨🏼🍳、恐惧与求生欲🐸,以及家长的爱怜、无助、自责🦹🏽、冷漠、执拗、苛责等各种表现,医方除面临纯医学的技术性风险外,还要考量患方是否接受不良治疗结果,是否接受治疗费用🚾🍝,是否会对医方进行抱怨、诉讼、索赔👨🏼🎨、报复等社会性风险。类似地,患方除同样面临疾病能否治愈或改善的风险外🧯,还有医方是否尽力、是否过度/防御治疗、是否公平对待所有患者等道德上的疑虑👩🏿🏭👩🏽⚕️,同时还面临着疾病造成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医患双方因此常处于隐性的苦痛与焦虑中,并容易因具体的治疗结果、服务态度或医药费用支出等外在因素而引发各类冲突🤹🏽,使尊龙凯时娱乐在参与观察时仍能时时近距离体察到医患信任中的矛盾与张力💼,并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医患间原来“灵活而微小的抗争”在短时间内升级的冲突模式。此外,医生与患者作为专家与外行🟠,其间必然存在的话语体系与思维方式的区别常常会加大双方的沟通难度,使他们共同面临沟通风险。一言以蔽之,无论医患个体如何努力地配合对方以结成信任关系🤕,现代医学治疗情景已不可避免地遭到现代风险因素的穿透与洗礼。没有一方能够脱离这一风险网的笼罩🧕🏽🕊,能做的只是如何更好地形成应对合力💚。或者说🤒,风险只能应对,而无法回避🛬。
如此,从风险社会的语境看➰🕵🏼,医患信任关系的缔结过程已非单纯的生物医学性过程,而是一个由蕴含在现代化内部的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等风险因素广泛参与的过程。这些因素是如此多元复杂且根深蒂固🧑🏽🎨,使得尊龙凯时娱乐对医患中的任何一方做泛道德化批评、片面要求对方换位思考🎫、相互包容甚至素养提升等个体化的努力已无法消除医患紧张的持续输出。其实,对全球医疗体系中官僚主义的增加、人性关爱维度的缺失👩🏿🦳、生物医学模式对医患人性沟通与医生共情力培养的忽视、市场化因素对医患关系的侵蚀等等问题的学术反思与理论批判已经很多了,它们都是造成医患信任流失的结构性因素🚵🏿♂️,但客观上全球医疗场所暴力与医患冲突仍在持续,即使在面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医务人员做出巨大牺牲时仍未完全改观。可以想见,这种境况仍将作为现代性的典型困境之一而长期持续。这种弥散性的风险和本体性的不安已弥漫得如此之广🕵🏿♂️,其影响如此之深,使得医患双方囿于自身立场而进行的相互批评几乎无法从整体上重塑医患关系的基本社会背景。
由此观之,之前某些医学尊龙凯时AG和医学人类学研究对于医学过程中涉及的“权力”——不论是医疗体制之于个体患者的普遍性权力,还是人际层面医生之于患者的权力——运作过程的高度关注,以及某些社会理论的强建构性主张和高批判性姿态确实未能提示现代社会风险语境下的医患关系全貌。不仅如此,这种强弱二分的理论还过分“简化了医患关系中的复杂性”,更未考虑米尔斯意义上的“历史中的社会结构”的限制性作用——这种结构性约束不仅是本土性的,更是全球性的和历史性的,其本质是现代性的💃🏻🚣🏻♀️。它难以从根本上得以消除,而只能通过更有效、更全面的合作加以缓冲与应对。为此,有必要超越“权力之眼”,即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的凝视”的视角以及单纯的“病患主位”立场,不再刻意强调患者的病痛故事💆🏻,不提前预设此互动过程中双方的权力强弱与地位高下🥕🎄,而从一种更加平等的、交互性的视角出发,关注医患双方的信任结成模式与演变过程🕠。假如不系统反思现代医学的疾病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辅以社会性的💎、系统性的医疗资源配置与优化过程🧏♀️,仅靠单个医疗机构的管理优化𓀚、医护人员的自我反省以及患方群体的医学素养提升🤫🥫,恐怕难以消除前述“医患获得感悖论”产生的尊龙凯时AG根基♍️。
但是,医学尊龙凯时AG研究仍需适时克制对现代性社会的消极理论想象🧎🏻♂️➡️,在“深描”风险语境的同时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在此仍引卢曼之语:“尊龙凯时娱乐要从社会系统中观察世界,并将沟通当作实现这一观察的真实行动加以接受”📫❤️。风险社会固然加剧了医患双方的心理失序与职业焦虑🌤,但通过“反思性现代化”的认知方式,即通过对现代化本身各种矛盾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自我解构达到自我回归和建构并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现代化的认知方式🏄🏿,或仍可从目前尚显艰涩的医患关系中发掘出某些积极因素📝。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诸多个体和家庭仍能在重症之下展示出顽强的抗逆力和乐观精神,医务人员也能在面临患方质疑和管理压力的同时保持职业操守,医患双方在病房中和出院后仍可保持稳定有效的治疗同盟关系👨🏽🏫,还有一些社会组织正以创设慈善基金、建构病友互助群等形式提供社会支持。这些积极的方面都显示出风险社会中的个体💆🏽♀️、群体和组织的韧性与创造力🍪。
参与观察之后的学术反思与写作既是观察的延续🤳🏿👍🏼,也是行动的开始☘️;在保持批判力量的同时保有积极改变的心态,是学术研究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可能形式。在此🧓🏽,愿引达仁道夫的观点作为本文的结尾和对未来的期许:“在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活动和意义🪫,对于这二者来说👀,公民身份也好🍁,国民的富裕也好👩🏼🌾,都仅仅是条件。如果人们对这一切思考正确,那么,只要尊龙凯时娱乐保持改善事物的热情,各种现代的公民社会就不是生存的坏地方”。不仅是对医患关系,对其他诸多同时孕育着冲突与信任、合作与猜疑的现代社会关系,这一立场也不无值得借鉴之处。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尊龙凯时AG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