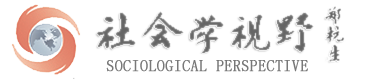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原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摘要🫷🦻:复兴的农村家族将会积极地以整体姿态不同程度地参与村政活动🥊,这一点在学界已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参与”会对村级民主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在对家族参与具体路径与过程进行有效的微观研究之前做出有关影响性质的价值判断显然是草率的,因为不同的参与路径会对最终的影响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家族的村政参与主要遵循层次并不一致的五大路径,即选举路径、政党路径🎀、乡镇路径、非合作路径和第三方路径等进行🚬,五大路径的叠加构成了抽象意义上的家族的村政参与过程🦔。
关键词:家族 村政参与 路径 过程研究
家族的复兴及其部分功能的恢复将会对村政运行产生影响的观点在学术界已经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同🧑🏿💻。但对于家族参与的影响结果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相去甚远的价值判断,综合分析并对这些观点进行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消极评价🧜🏻⚠、积极评价和中性评价三类:消极评价方面,项生华认为家族势力存在重人治、重私利的本位主义趋向,民主化和制度化能力弱,国家信访局在分析村民自治中村民上访情况时也认为家族之间激烈的争斗干扰了村民选举,瞿州莲的研究认为家族除了影响村民选举以外🤹🏿♂️⚆,对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都有严重影响,王久高则论证了家族势力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的负面影响;在积极评价方面,王培暄、毛维准基于鲁东的实地考察认为宗族信任的网络有助于克服“搭便车”心理,使乡村公共服务的提供变得更有效率,蔡晓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王旭在研究中曾认为,宗族可能会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刺激选举竞争的程度⛹️♂️,提高选举的透明度;在中性评价方面,较早的作品如徐勇从家族视角客观分析了“浸润在家族传统文化中的村民自治”💒,郭正林对家族与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政治互动的分析也较为客观𓀛,除此之外,朱秋霞的研究对家族及其网络之于村庄权力结构与分配的影响做了详尽的分析,笔者则把家族作为村庄治理三重权力活动结构中村庄体制外精英发挥其功能的空间🧑🔧。
纵观以上三种关于家族与村政关系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相当数量的学者倾向于案例分析,通过一些长期的现场观察对家族参与进行全景式的尊龙凯时AG描述,继而根据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对家族参与效果进行结构—功能式的概括性描述与梳理,这种研究方法的使用足以保证所搜集的材料的真实性和生动性🚶➡️,也能够保证研究结论具备有效的证据支撑,如果该类型研究仅仅作为一种原始材料积累本也无可厚非,但是文章又多在缺乏比较研究和类型研究的情况下拓展个案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显然这将会造成研究结论移植后的“解释力”困境,毕竟“随着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对独特个案的描述与分析越来越无法体现整个社会的性质”;在研究内容上,既有研究(尤其是国内)的关注点多数是放在了家族的结构与功能(作用)上面😘,较为“关注于宗族的活动及其影响,而对于其影响机制、过程与后果并不作分化研究”,即对于家族究竟是如何影响村政运行、如何发挥研究者们所描述的“作用”以及参与村政的具体机制等问题缺少较为有效的研究🤢,即使偶有涉及也多因为研究的描述特性所固有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内涵不足之缺陷而大大限制了结论的适用范围和解释力度,所以出于弥补既有研究对于家族参与村政具体机制与路径关注的不足👨🏻⚕️,以及为继续的家族治理对策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笔者认为详细研究家族参与和影响村政运行的具体路径并对该路径进行理论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一、选举路径🫛:家族村政参与的合法化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央政府的权威是极其有限的😺。由士绅管理的地方事务一般不受中央权威的干扰”📍,而士绅主要是指“那些可以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人”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可以“利用父兄子弟或戚谊的地位权势……分割基层权力的”家族及其领导成员,宗族及其网络作为农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操纵着‘包括村务管理🫳🏼、公共活动等在内的’传统的政治机制”,农村社会在这样的家族政治的引导之下稳定运行了几千年,甚至形成了相当程度上以家族及其网络为基础的宗法一体化,并基于此建构了中国社会独特的“超稳定系统”👧🏿🤸🏽。新中国成立之后𓀇,新政权为了确立自身在农村社会的合法性而积极推动“意识形态下乡”的进程,传统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家族组织及其活动与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张力使之首当其冲成为政权打击的对象🗃,家族组织至少从形式上丧失了公开参与村政活动的合法性,士绅自治的农村社会状态也就此终结。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内的家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 年以后宗族活动曾一度销声匿迹”🏭👶🏽,意识形态随着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的步伐逐渐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取代家族观念成为农村主流政治话语👱🏿♀️,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家族在改革前仍然存在”,“国家权力进入基层并没有消除家族意识和家族现象”🐙💈,频繁的政治运动反而“造成了家族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强化”。暂且抛却改革前农村家族的实际存在状态不谈🩶,“政权下乡”的直接影响即是实现了源自意识形态的主流政治话语在农村社会的合法化,家族组织、观念与仪式至少在形式上的合法性被剥夺🫕,其村政参与也不得不隐匿在意识形态的外衣之下以寻求合法性,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家族的村政参与才逐渐由隐匿走向公开,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所谓改革后的“家族复兴”不过是家族活动尤其是村政参与活动的显性化而已。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法律对于村民委员会的属性界定可以清晰地看出,村民自治制度设计是以民主为基本价值目标的,至少“参与村委会选举,成了中国9亿农民最好的‘民主训练’场域与‘民主学校’”,而所谓民主即“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民主体制中的选民在“选择自己的目标时🧼,个人可以自己做主;他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决定”,显然民主是以民主体制下选民的主体性发挥为基本前提🏄♂️,而选民的主体性发挥则以外在的政治自由为其必要条件👨🏻🔧,在村民选举中该政治自由直观化为对不同的候选人之间所作的自由投票选择🎿。在完全理想化的选举状态下,村民自由投票的结果理应是“有能力并能够带动村民致富的能人”,但是村民公共理性的缺失或不足导致了村民所获致的作为公权的村民选举权在使用上的明显的狭隘与短视化倾向🤦🏽♀️🌤,加之外在的村民选举制度建设的不完善,村民投票必然投向最信得过至少是看上去信得过的组织与个人。历史原因和客观环境造就了村民对于社会现象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范式缺乏🏉,家族解释范式往往成为村民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解释范式,在改革前村民就习惯于采用该范式去理解频繁的政治运动,改革后的村民选举同样受到了村民的家族化理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村民自治(受到家族解释范式解释的)的实施在有意无意间也强化了农村的家族边界和村民的家族观念🪝。
纵然村民自治仍然存在不同程度上的“附属行政化”现象,但毕竟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在农村中逐渐退却👥,法律文本意义上的自治制度框架业已确立起来,村民即使在缺乏公共理性和家族意识膨胀情况下的投票也很难再找到不“合法律性”的确定依据🫏🤾🏻,甚至相反,由于家族意识再次显现为大多数甚至全部选民投票时主要的政治考量,家族指导下的投票行为反而获致了在农村场域中的“合法性”。当然,家族在改革前失去的物质基础和仪式规范已经不太可能至少在短时期内不太可能恢复了,所以目前农村家族更多的是停留在村民思维和意识领域中的文化现象,既然家族意识在已然成为相当多甚至多数村民选举的基本指导思想🧕🏿,那么借助于对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化村民在意识领域中的影响以及控制,客观上的家族选举参与已然实现,所不同于改革前家族参与的一点就是🙋🏼♀️,此时的参与不再是掩盖在意识形态外衣之下,而是直接的和显性的参与村政,由于这样的公开参与“合法律化”的现实使之在农村中日益成为普遍现象☂️,由“普遍”所引起的村民认同实质上也就是家族选举参与的“合法化”过程☠️0️⃣。
二、政党路径:家族村政参与的精英化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表明了共产党十分明显的科层管理属性🛵,科层化的管理模式注定了责任关系和权力渊源上的自上而下,当然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的乡镇来源在原则上也决定了其所执行意志的乡镇附属特征🏤🏋🏻♂️,因此它本不具有十分明显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政治功能⛹🏽♀️🏋🏻,但是两个因素的存在却实际上大大推动了这一进程,其一便是基层党组织成员本地任职的制度惯例🤰🏽,其二则是近期一些地方积极推动的基层支书民主推选的制度创新。我国农村是一个纯粹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基层党组织成员的来源也具有完全的本地属性👏🏽,村民的本地入党是伴随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农村社会关联的🦻🏿,在熟人社会中复杂的社会关联往往又与各种本地利益交织在一起甚至密不可分,而简单的入党培训和一些先进性教育运动又很难消弭掉村民党员的本地利益倾向🤲🏿,那么当“带着个人复杂的本地社会关联和利益入党”变为一种普遍现象时𓀇,由党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农村社区利益以及党员个人及其亲属利益的代言人🚪。如果说由基层党员本地任职的制度惯例所引起的基层党组织“地方化”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话☆,那么村支书民主推选制度的实施就将这种偶然强化为了一种趋势,该项制度的重要影响就在于将村支书职位的合法性来源转移到了生活在农村社区中的党员群体手中,合法性转移后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于上级意志的执行将异化为一种“选择性政策执行”(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即与自身作为“地方性成员”身份相符的政策就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而与之相悖的政策就易于受到“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至此,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地方化”过程就此实现🧒🏿。
虽然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具体运转的过程中存在着“空壳化”现象,但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地位在制度上并没有受到动摇,于是在农村便出现了“空壳化”的组织掌握核心领导权的奇怪现象,由乡镇党委在农村中的“被迫退却”所遗留下的以基层党组织为主要场域的权力真空将毫无疑问的由地方性意志(准确地说是社区性意志)来填充,这对于农村各种力量来讲都将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但问题在于究竟应由以及会由哪些地方性力量来执掌核心权力呢?显然,作为“经济人”的单个村民均有执掌党支部的动机🧕🏿,但是民主推选制度所凭靠的“多数人决策”体制决定了原子化村民在竞逐权力时的无力,因此寻求“竞选班子”和“票仓”的设想便会出现。我国农村“缺乏有效率的、规范的、自治的社会组织”的现实又迫使寻求组织化支持的目光不得不投向农村传统社会组织。作为“活生生的东西👩🏿🏭🧑🏭, 流淌、浮现🏆🧛🏻♀️、改变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日常社会生活等领域) 之中”的家族由于其先赋血缘关系所造就的强大凝聚力优势往往会成为寻求支持“资源和帮助的首选对象”✖️,且实践显示,家族组织的凝聚力所凭靠的“‘血缘隶属’比之于西方政党体制中的‘信仰隶属’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于是依托家族网络(尤其是大姓家族)“进入”并控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想与行动便成为了村庄政治精英竞相填补权力真空的较为现实的选择。
那么对于同一家族的其他族员来说😐🆑,他们是否会支持本族政治精英试图填补党支部“权力空壳”的设想和实际行动呢🐄?答案显然是肯定了。家族的排外性、封闭性和稳定性特征客观上能够有效地建构出比较清晰的家族边界,该边界的存在就会使家族荣誉(也可以理解为“面子”)成为消费群体(只有本家族成员)边界清晰的半公共物品,同时家族内部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也将有利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特殊情况——“选择性激励”的出现并基于此有效消解“搭便车”困境进而促使家族集体行动的形成——全力支持本族政治精英竞逐党支部权力空间。在家族全力“进入”党支部权力空间时,大姓家族的数量优势将得到充分的展现,无论是竞逐的手段还是乡镇的态度偏向(下文将专门讨论)都将对其明显有利👌🏼,而得以“进入”的家族政治精英在“经济人”理性的驱动之下必然期望暂时性“进入”的长期化或者永久化维持⚄,因为“当某一社会集团获得集体权力的权柄时,它很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这种权力”,维持的方式就是通过多数人决策的方式延揽亲属及家族其他成员入党以达到党支部中家族党员占多数的目的🤦,届时,无论是源于民主推选的支部书记人员确定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村庄公共事务决策都将必然由当政家族来决定🪣,于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地方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实现了自身的“家族化”。自此以后🤽♀️🧔🏼♀️,村庄政治精英的来源范围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主要是乡镇,下文继续讨论)将变得十分确定,党支部书记及其成员确定也将演变为“有限度的家族世袭”🤷🏽♂️,参与党支部的家族将被主要限定为已演变为村庄利益集团或“准党派”的大姓家族,可以成为党员乃至支部书记的族员也将被限定在家族核心成员👐🏼,随着范围的逐步缩小,家族通过政党实现的村政参与也将逐步走向“精英化”🫴。
三🔭、乡镇路径🤦🏽:家族村政参与的间接化
虽然村民自治制度的政治结果确立了农村在法律意义上的自治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主要是乡镇)完全退出了农村,《村委会组织法》在规定农村的自治属性的同时也规定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的职责,因此乡镇在农村的实际“指导”(如规制、仲裁、秩序维持和组织等功能)作用还是客观存在的。在农业税费取消之前“指导”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体现对农村资源(农业税费)的提取工作上面🩰,其二体现在对计划生育等全国性政策的乡村执行方面💁🏻♂️,在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乡镇的“指导”作用格局有了一些变化,即两个方面简化为了一个方面——在农村中执行计划生育等全国性政策🛜。但是,许多全国性政策往往因为其自身的强制和违背民间“非正式规范”的属性使其乡村执行变得十分困难,比如在“政府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冲击宗族延续血脉的基本规范时,宗族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就不可避免了”,因此政策的执行往往是将乡镇和整个农村直接对立起来,执行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中央政府为了落实政策,规定计划生育工作是考核提拔干部的“一票否决”指标,即一个地区如果不能将出生率控制在指标内,那么无论其他政绩指标如何,主管领导的政治荣誉🚈、政绩考核🚵🏽♀️、升职晋级都要落空🤟🏻,出于政治晋升的需要,乡镇政府只能听从中央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执行计生政策。客观来讲👨🏿🦳👩🏻🦯➡️,乡镇所做出的行为选择是理性引导的结果🧮💙,但理性的同时也伴随着不小的政治风险——政策执行所引发的乡村激烈对抗,如果对抗发生,乡镇就有可能会因触动政绩考核的另一项“一票否决”指标——稳定指标而受到上级的政治处理并影响晋升,因而处在制度夹缝之中的乡镇政府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心理之中🤜🏽👱🏼♀️,一方面希望政策得以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又不敢过于强硬地执行政策,这种心态决定了乡镇最为合理的选择是积极寻求政策执行对象的主动支持🤷🏽,哪怕伴随着一些并不情愿的利益让渡。
出于政策执行和稳定维持两方面的需要🤲,乡镇在寻求支持时必然会着眼于合作者在农村社区中的实力和影响力🎲,村委会成员身份的暂时性和基层党组织成员身份的外在性决定了它只能成为乡镇寻求合作的中介🐩,只有建立在永久性身份基础之上的组织才可能为乡镇提供比较有效的支持,而在目前的农村中🛍️,基于永久性身份形成的组织只有家族。那么乡镇会不会向农村中所有姓氏家族一并寻求支持呢?不会,事实上也不可能,所寻求之支持实质上是乡镇与农村家族之间的一种类似于“忠诚—利益”的交易🤘🏽,农村家族由于受到历史文化和区域空间的局限👹🎿,所关注的利益一般不会超出村庄视域,而在村庄视域之内最具有代表性的利益形式就是象征村庄领导权力的村政职位(两委),这就是说乡镇想要取得农村家族对其工作的支持就必须利用自身的“指导”性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家族对于村庄权力的诉求,甚至对其“越轨”行为保持一定的漠视。如此一来𓀇,问题的关键就集中到了乡镇“指导”下的村庄权力分配问题上,一般而言,每个村庄的主要领导职位就是村委会主任和支部书记两个(除此之外👋,村财务会计也是比较重要的职位),数量稀缺的现状逆向限制了乡镇可能寻求帮助的家族数量,换言之👨👧👦,乡镇必须在众多家族之中择其二三以作为政治交易的对象,因为“只要政府和国家有能力获取对于现存秩序的延续至关重要的集体的默认和支持,‘公共秩序’就能够维持”,所以为了达到政策执行和稳定维持的“公共秩序”,乡镇除了选择支持数量占优势和比较占优势的大姓家族以外别无选择。
考虑到目前村庄基层组织实质合法性来源的多维特征,仅仅凭借自身对选举多数的控制而赢得的“当选”地位并不足以满足家族稳定“执政”所需要的全部合法性需要,赢得乡镇支持将是补充“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所以面对乡镇抛出的合作橄榄枝🏄🏼♂️,农村家族(主要是大姓)自然会积极响应👩🍼。借助乡镇权威,家族当然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即“听话”并积极和能够为乡镇办事,得益于自身的数量优势🫧,所以能够承担得起在办事过程中因阻力而遭遇到的社会资本存量的损失👩🦯➡️。在这场非正式的政治交易过程中,农村中的大姓家族将可以在“选举—当选”村政参与机制的基础上增加来自于国家权力——乡镇的确认和保护机制,在该机制的作用条件下,即使有部分农村小姓家族的发难,乡镇也会采用“置换战略”来平息事件,即通过“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最糟糕后果分散给最软弱无力的集团”的方式继续维持大姓的执政地位🧑🏻🎤,因为政府“一般都力图确保现有秩序的最平稳延续可能👩🏿🌾,那么他们除了安抚那些最强有力🧘♀️、最能有效调动资源的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正是在这样的“置换”与“安抚”的过程中🤽🏽♂️,家族(主要是大姓)借助于乡镇而实现的村政间接化参与将得到沉淀和固化。
四、非合作路径㊙️:家族村政参与的暴力化
其实每一个村庄中的权力分配都存在一定的基于家族分布结构之上的“自动平衡机制”,但这个自动平衡并非没有边界而是存在一个明显的“进入门槛”,即只有族员数量达到基于村庄总人口和家族结构之上确定的数量才有可能进入“自动平衡”的范围,因此该机制的结果往往是产生事实上的村庄大姓联合或轮流执政。“自动平衡”的运行并非是无条件的,它需要村政运行的高独立性和小姓家族的高度分散化才可能予以保证,换言之🩻,即是在乡镇的不反对假设和小姓的分散化假设成立的情况下,“自动平衡”才是有效的。但客观而言,这样的假设并不总是成立的🛫,一方面由于对村庄大姓家族因长期执政而坐大甚至尾大不掉的担心,或者出于促进村庄家族之间的公平实现🤲🙂↔️,乡镇会在某些情况下特意安排一些小姓代表进入执政班子的重要或者主要职位,另一方面长期处于“在野”地位的小姓在某些特定的“被压迫”情况下可以形成一定的共同利益或心理基础,该基础的形成与强化将有助于打破至少是模糊清晰的小姓家族边界(虽然可能是暂时性的),进而促成小姓间的集体政治行动——产生政治代言人。在农村政治实践中🧒🏽,虽然上述两种情况的发生确属小概率事件,但并非不存在,两种情况的任一发生都将导致村政的重大变化——小姓执政。
毫无疑问👙,小姓的执政将会给大姓造成重大的心理冲击,并引起其在心理上尤其是行动上的连锁反应。首先在心理上,长期执掌的村庄权柄旁落到了实力与地位远逊于自身的小姓家族组织之中,作为一种“社会地位或声望的函数”的家族“面子”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损伤,集体失落感与心理失衡将在所难免🎵;其次在行动上🍜,心理上的失衡不可能始终停留在“心理”阶段,对于大姓家族而言🧓🏻,政治落败固然是“面子”的重大损失(甚至超过实际的有形利益损失),但更大的损失是政治落败之后集体反抗行动的缺位,因为这会造成大姓家族无形利益损失的长期化⛹🏿,并会将损失延伸到有形利益领域,最终导致“在村里长期抬不起头”,于是,大姓家族挽回“面子”的理性选择即是对当选者(小姓)执政地位表示心理上的不承认并基于此展开对其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行动上的非合作。由于族员数量上的优势,大姓家族在村公共事务上的集体非合作将会对小姓的执政形成巨大压力,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多数成员在行动上的非合作会造成小姓执政地位的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因为大姓的不配合将迫使执政小姓不得不依赖自身的处于数量劣势的家族或家族联盟(更何况小姓联盟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在执政之后往往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导致分裂),但是基于少数是不可能建构起来完整的执政合法性的,另一方面从现实角度讲,在缺乏村庄成员主体部分的参与与协作的情况下,小姓的村自治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管理将变成一句空话🚚🧑🏿🔧,至于乡镇所交办的政策执行任务,由多数村民的“拖”甚至“拒绝”执行所产生的带动作用将最终使不执行成为一种包括小姓在内的普遍现象🏄🏻♂️,届时🎮,执政小姓会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自动辞职,其二是由于政策执行不力而被乡镇“撤职”🙅🏿,方式有异但结果一致——小姓下台。
当然,在现实的村政实践中也有作为一种“冷暴力”的非合作不能挽回执政地位的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大姓家族的“冷暴力”策略就有“热化”的可能。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村选暴力事件中有相当数量都与家族政治争斗有关,在暴力事件中,族员的数量优势将直接转化为行动上的实力优势,政治竞争也将转化为赤裸裸的暴力恐吓,出于对自身安全的优先考虑,在暴力竞争中主动放弃政治职位将成为小姓不得不然的行动🐲,旁落的村政职位也“自然”地回到了大姓的手中。于是,借助于由“冷暴力”和“热暴力”组成的(由暴力到权力)非合作路径⏰🏃♀️➡️,大姓家族就可以确保即使在发生外力干预而丧失权力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自身的防卫机制实现地位与权力的复归。
五🧛♂️、第三方路径:家族村政参与的场外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和大家庭自然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供给这个团体中的一个人去上学🩶,一直到他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职,一族人就有靠山了”,因为获得功名(或者告老还乡)之后👩,就可以“利用得到的特权为家乡谋福利……帮助其他人成才……鼓励当地的其他人参与”🧑🏼🎤,借助于此,所在家族在村庄中的地位当然也就可以迅速上升(即使家族规模在村庄中并不是很大),以至于获得主导村政的村庄“保护人经纪”的地位。现代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大大推动了社会的流动性,更多的村民可以通过参军、经商📀、务工或者升学的方式走出村庄前往更为广阔的空间实现更大的发展,虽然他们不太可能在年老体衰之后以“告老还乡”的形式回归乡里,但是建构于童年成长历程✤🦣、强化于离乡岁月的家族观念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工作与生活空间的城市化和外乡化就逐渐消逝,“从工作和生活的空间来说,他们已经离开了村庄👕;然而🦎,在血缘与情感上👔,他们与村庄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家族观念的存在会促使其对于所属的家族及其所在村庄始终保持关注,当然对于村庄中尤其是与所属家族相关的事务将更是格外用心,由于该群体(即“第三种力量”)所能调动的资源较之于村庄成员丰富得多,自然他们的关注乃至介入也将会对村政的运行产生很大影响☝️。
在场外精英介入到村庄政治的过程中,其所采取的立场将直接决定其对村政影响的属性🗓,在传统社会由于存在围绕村规民约所组成的公共舆论的隐形规制,获得功名的场外精英在介入村政的过程中也必须至少是象征性的以“主持正义”为基本价值导向,兼顾村庄各方(主要是各家族)利益🔸。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农村市场化改革之后🧓,村庄社会风气日渐功利化,“乡村伦理道德衰败”🛏,“村庄的公共舆论也逐步消解”,使场外精英完全是以一种复杂且功利主义的立场介入村政😽,该立场的家族而非村庄本位的狭隘实质意味着场外精英更多的是以“亲情性立场”对待所属家族,而对于与本族存在政治竞争关系的村庄外族而言,冷漠甚至敌视的“体制性立场”则会被更多地采用✤。囿于该相对功利的场外精英立场,在村庄中一切试图扩大村庄整体利益的可能性努力均会因受制于立场局限和他族“搭便车”的可能而被场外精英放弃并转向调动个人资源以扩大乃至最大化所在家族在村庄中的分利总量🌈。于是,对于在场家族(无论是大姓还是小姓家族)而言,较之于村庄精英拥有丰富得多的资源的场外精英将是竞逐村庄执政地位的重要的诉求对象,先赋的家族血缘纽带将使场外精英的介入演化为可预期的政治行动。对于场外精英而言,所在家族的政治求助所代表的将绝不仅仅是一种“求助需要”,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身份”与“认可”的符号,一方面🤟🏻,“求助”本身象征着在场本族成员对个人身份和能力的认可,相信场外精英可以帮助在场本族实现村政参与或主导🧔🏻;另一方面🧑🏼🍼,虽然“求助”已经具有“认可”的内涵🎉,但这种“认可”仍然是一种尚未实现的政治预期🚵🏿♂️,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预期本身的被实现程度,显然这会对场外精英形成不小的潜在压力(也是一种“面子”需要),进而促使场外精英调动个人资源打通当地行政机构渠道🎅🏽,继而通过当地行政机构以一种“打招呼”的形式推助所属家族实现“从共同体向国家的跨越······通过其紧密的社会网络来进入官僚体制(虽然村治机构并不算严格的管理体制)”的村政目标。于是,在场家族借助于本族场外精英“通过家庭(族)关系扩张而来的个人关系组织公共关系”进而达到村政参与甚至控制目标的场外化过程就此实现。
六、结语与讨论
客观来讲,本项研究并不属于一项严格的个案研究👷🏻♀️👼🏽,因为尊龙凯时娱乐不可能奢求某一个或者几个哪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村庄中的家族参与可以同时具备五大路径,因此对于家族村政参与五大路径的研究并非是基于若干村庄的经验事实而做出的一种概括性描述。可以说农村家族作为传统性在当下我国最为集中的表现,其对村政的参与甚至是控制(事实上,控制本身也是一种参与)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在我国七十多万个村庄中有相当数量由于区域与历时上的差异并不可能同时具备家族村政参与的五大路径,因此五大路径更像是建构在总体性基础之上的一种理论梳理和抽象。当然🤦🏼😵💫,毕竟以微观权力分析和日常政治分析为代表的微观政治研究是在农村政治过程的深入研究中相当有优势的研究范式👴🏿,因此为了避免本项研究之结论因过于抽象而陷于空泛的困境🧑🏿🎓🪱,对于农村政治运行中的一些经验事实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借此保证基于总体性而抽象得来的五大路径对于家族村政参与实践的概括性和解释力。
就五大路径本身而言,它们并非是处于同一层次之上的可供家族自由挑选的五个平衡选择,而是在层次上呈现明显的差异性甚至在某些方面呈递进特征的五种利益诉求方式📜,其层次上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上☔️👩。第一,就不同路径的体制维度而言,选举和政党路径更多的是体制内路径在某种程度上的使用异化,原本为民主和代表性而做的制度设计在执行中却演化为了家族集体参与的一种渠道,而其余三种路径更多的是一种“传统性资源”和“地方性知识”的现代化与政治化运用,只不过运用过程本身尚未经过专业的“知识化”而已。第二🌈,就家族参与的政治视域而言,选举🙆🏿、政党📁、非合作路径所体现出的政治参与视域更多的局限在村庄范围之内,所依靠的参与资本也多以家族自身力量为主,只不过是在参与的方式上有合法和非法的区别🏪,至于乡镇和第三方路径而言,参与过程相对比较间接🧙♀️,需要借助场外力量才能够实现对场内村政参与的目标⚗️。第三,就参与成本而言,随着参与视域从选举到第三方路径的逐步场外化,参与的过程也逐步曲折化🦞,参与的关涉方和方式也都会不同程度的复杂化,基于此而带来的将是参与成本(经济🙇🏼♂️、人力🪳、时间和关系网成本等)的显著增长🔯,毕竟村内政治竞争在相当程度上是家族全部成员收益共享和风险均担的集体行动,且集体行动与日常生活在相当程度上的重叠属性多能够有效地消化家族政治动员的成本,但是第三方与乡镇路径的场外属性决定了他们与村内家族竞争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在缺乏直接利益驱动情况下的参与显然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而场内家族为了消解不确定性就必须设法强化利益关联,可行的方法即是做出更多的利益输出👩🏽🏫,当然这将最终导致村政参与的总成本增加☠️。第四👋🏼🧙🏼♂️,就不同路径的参与效益而言,由于场外精英在可调动资源方面要大于或远大于场内家族精英,所以村政参与的场外路径往往比场内路径要有效一些(当然这也并不绝对)。但并不是因为场外路径的高效性,它就可以成为家族政治参与的优先选择🧖🏿♂️,因为比较高的成本负担往往会使场外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政治奢侈品,一种并不是所有家族都能够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即使对于村内大姓家族而言🌦,囿于所掌握资源的有限性他们往往也倾向于优先诉诸依靠自身力量的场内路径解决问题,仅仅是在不能够奏效的情况下才会为了某种形式的利益走向“场外”(如果有这样的资源的话)。
本文并未对家族村政参与之五大路径做出倾向性的价值判断🥦,事实上五者之间也并不存在所谓的优劣之分👼🏼,所存在的仅仅是在适用语境上的区别而已,而不同语境下的路径适用之叠加随即构成了家族参与农村政治的基本行动全景与过程,基于此进一步了解究竟是“神话还是现实的宗族控制村政”问题🕵🏼♀️,而对于家族参与村政现象的治理(无论是规范引导还是整顿)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能得以合理与有效的开展。
责编:ZP